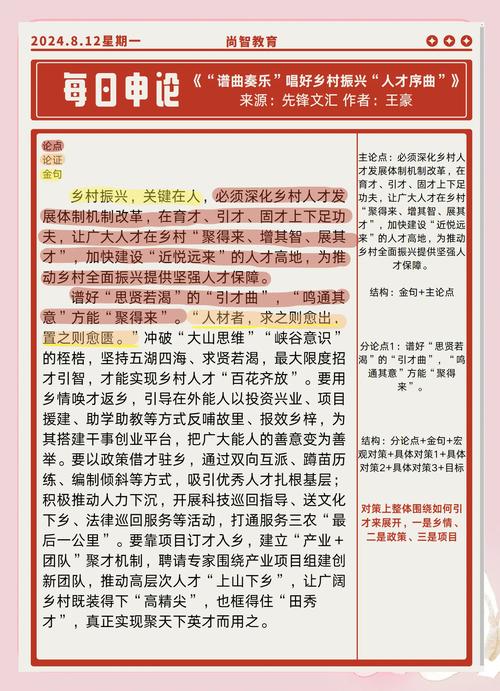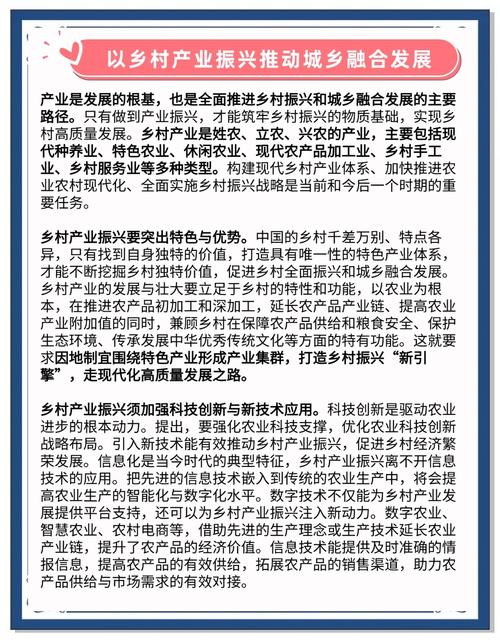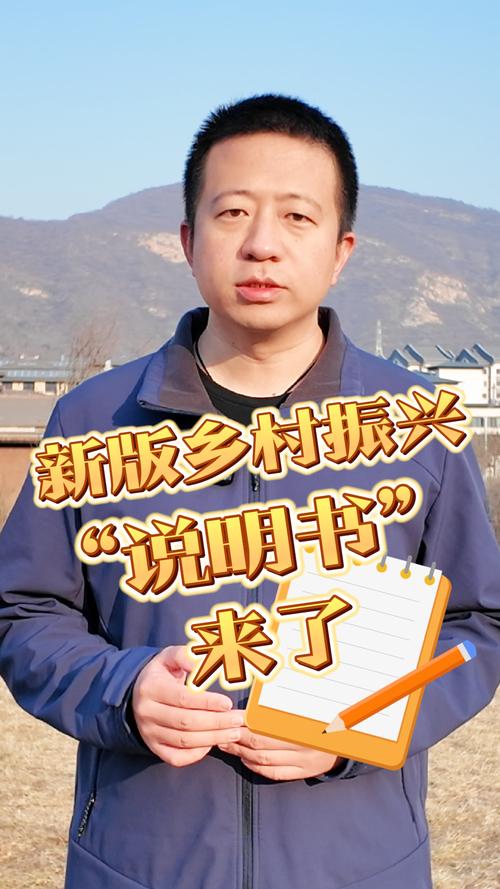在皖北平原的褶皱处,有个被芦苇荡环绕的村庄——张凤滩,这个户籍人口不足三千的村落,近三十年间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教育奇迹:连续二十六年保持适龄儿童入学率100%,培养出4位院士、27位博士和132位硕士,成为全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示范点,当城市教育陷入内卷化焦虑时,这座普通村庄的教育实践,为我们揭示了教育本质的另一种可能。
芦苇荡里的教育觉醒(1994-2003) 1994年深秋,村支书张守业在泥泞的田埂上拦住了准备外出打工的民办教师王素英。"素英啊,咱村小要是再走老师,娃们就得蹚八里河去外村念书了。"这句话让王素英把行李塞回床底,也开启了张凤滩的教育突围战。
当时的村小学是两间漏雨的土坯房,三个年级挤在同一间教室复式教学,村里动员返乡木匠张德旺修缮校舍时,这位老匠人将自家准备盖新房的大梁扛到了学校。"娃们念书是百年大计,我家房子晚两年不打紧。"1995年春天,村民们用芦苇秆编成围墙,用麦秸和泥抹出黑板,硬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建起了三间砖瓦教室。
师资匮乏的困境催生了独特的"教育合作社"模式,退休教师张明礼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县城,义务为高年级学生补习数学;在合肥读师范的假期,张春燕组织返乡大学生开设英语夏令营;村医李秀兰兼任自然课教师,带着学生在河滩辨识草药,这种全民参与的教育生态,使村小在2001年全县统考中首次进入前十名。
乡土课程的创新实践(2004-2015) 2004年秋,新任校长陈玉梅发现了个棘手现象:随着外出务工家庭增多,留守儿童出现严重的"文化悬浮"现象——既疏离乡土文化,又难以融入城市文明,她带领教师团队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课程改革实验。
"芦苇的腰杆为什么总是挺直的?"科学教师张建国开发的《湿地生态课》,让学生通过测量芦苇抗风强度理解植物力学;语文教师王翠萍将皖北童谣改编成识字教材,老船工口述的摆渡故事成为最好的写作素材;数学课上,孩子们用麦秆制作立体几何模型,用河蚌壳演练分数概念,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教学设计,在2010年获得全国基础教育创新成果奖。
最令人称道的是"家庭学堂"制度,每周六晚,村民家中轮流举办读书会,78岁的剪纸艺人张凤英教孩子们剪二十四节气图,拖拉机手张建军讲解农机维修中的物理原理,这种打破围墙的教育模式,使学校教育与社区文化形成有机共生,2013年,张凤滩小学毕业生平均阅读量达到城市学生的1.8倍。
教育共同体的建构之路(2016-2024) 2016年,张凤滩迎来教育发展的关键转折,面对城镇化加速带来的生源流失危机,村教育理事会提出"双向滋养"发展战略:既保持乡土教育特色,又主动对接现代教育体系。
他们与省城名校建立"影子教师"计划,每年选派教师进城跟岗学习,同时邀请城市教师来村进行田野教研,数学教师李卫国开发的"麦田坐标系"教学法,将解析几何与农田测绘结合,入选教育部精品课程,2020年建成的乡村教育博物馆,收藏着三代学生的作业本、教师手写教案和村民捐资建校的账本,成为鲜活的德育基地。
针对初中教育断层问题,村委会将废弃的粮仓改造成"少年书院",聘请退休教师开设晚间课业辅导,村民张大海主动让出自家院落创办"工匠学堂",教授木工、陶艺等传统技艺,这种立体化的教育网络,使张凤滩中学升学率连续八年位居全县乡镇中学榜首。
教育范式的当代启示 张凤滩的教育实践给予我们三点重要启示:教育振兴需要唤醒社区的文化自觉,当78岁的张奶奶用方言讲述治淮工程往事时,孩子们眼中的历史不再是课本上的铅字;教育资源整合关键在于激活内生动力,村民用卖芦苇的收益设立"教育反哺基金",资助完成高等教育的学子返乡服务;教育现代化不是对城市模式的简单复制,而是要实现传统智慧与现代理念的创造性转化。
站在村口的"教育丰碑"前,镌刻着三十年来所有参与建设者的名字——从捐出养老钱的五保户到义务代课的面点师傅,这座没有学术头衔加持的乡村学校,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教育的真谛:当知识扎根于生活的土壤,当学习成为社区的集体仪式,教育便自然焕发出超越功利的力量。
今天的张凤滩,晨雾中依然飘荡着中英双语朗读声,放学的少年们依旧在芦苇荡里观测候鸟迁徙,这个村庄用三十年时光证明:真正的教育振兴,不在于建造多少标准化校舍,而在于培育出尊重生命、连接土地、面向未来的学习型社区,当城市教育在焦虑中内卷时,张凤滩的故事给予我们重新出发的勇气——回归教育本真,或许就在转身可见的乡土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