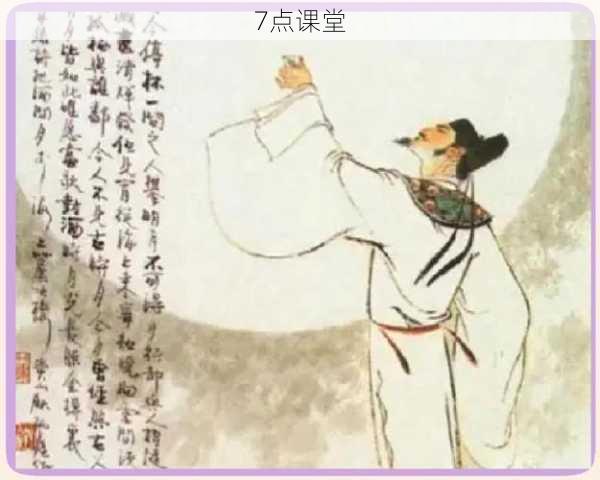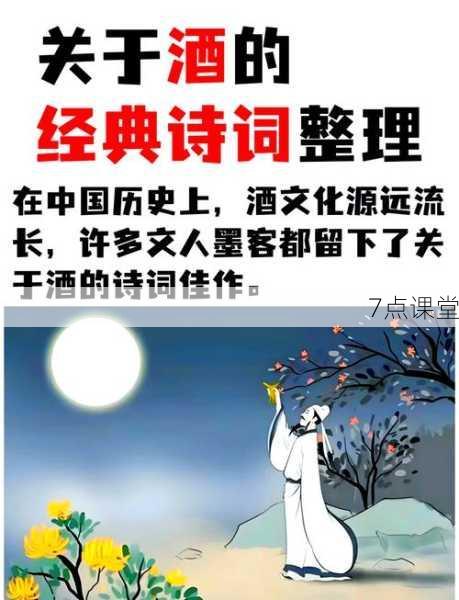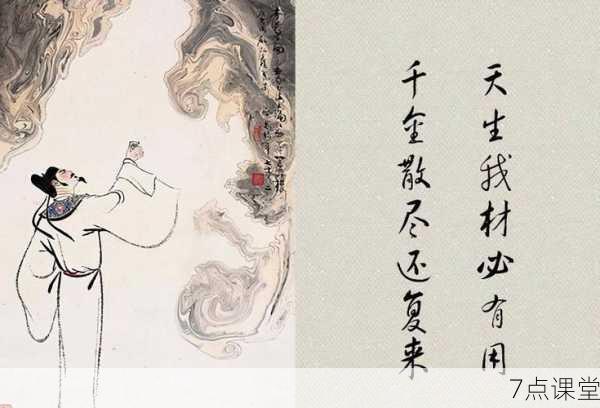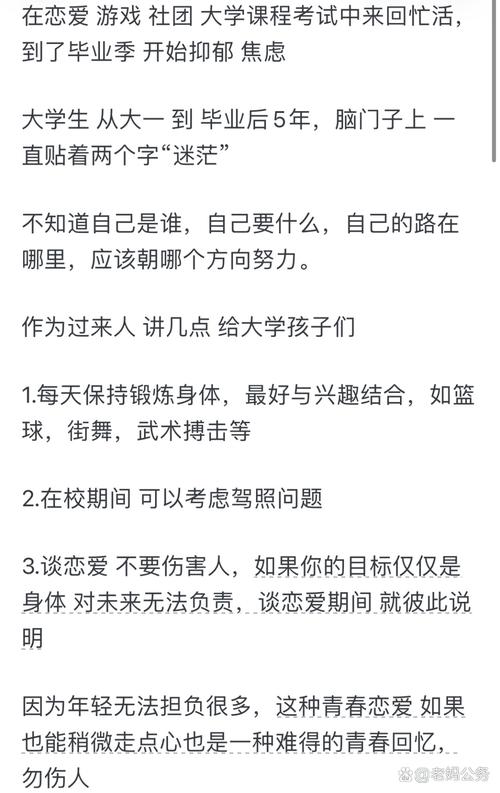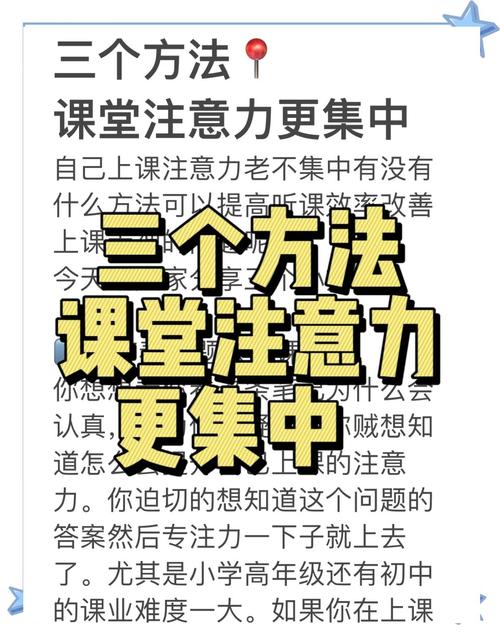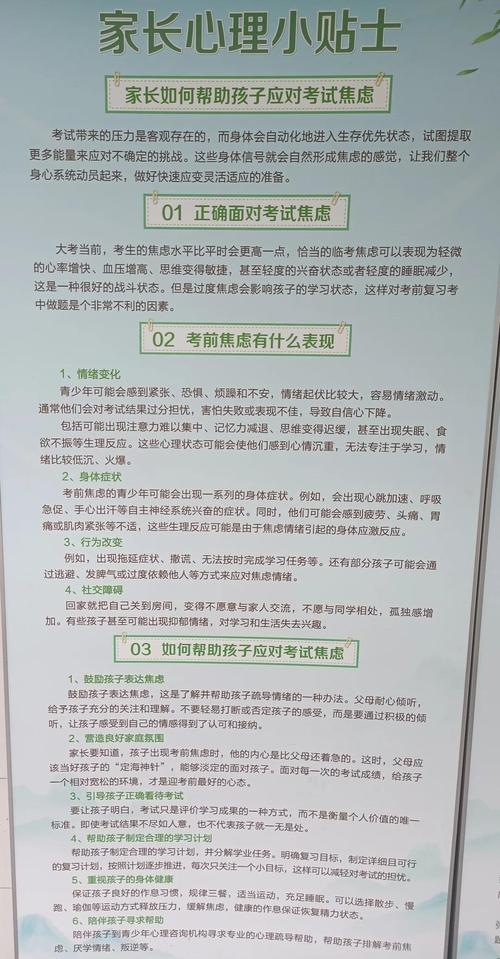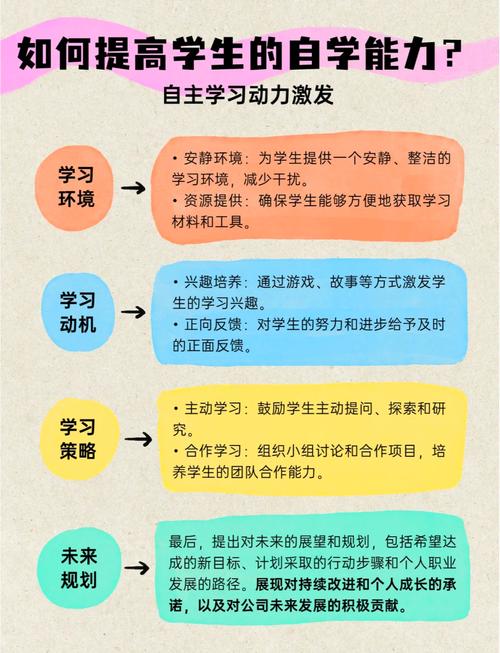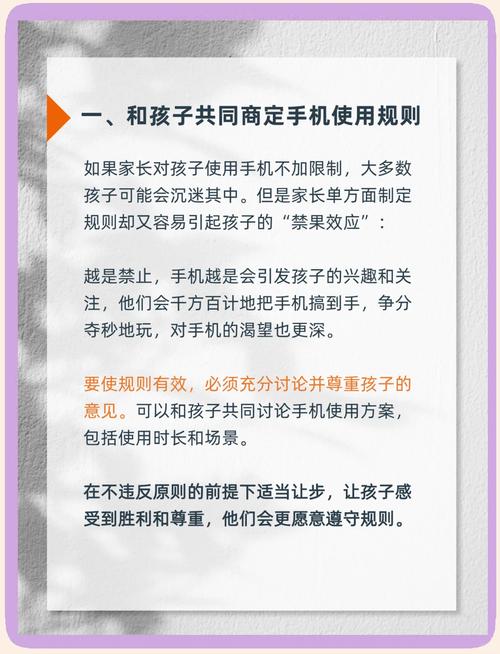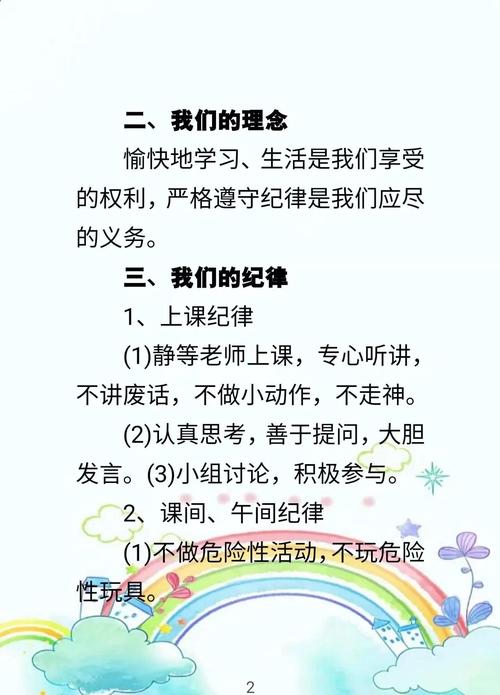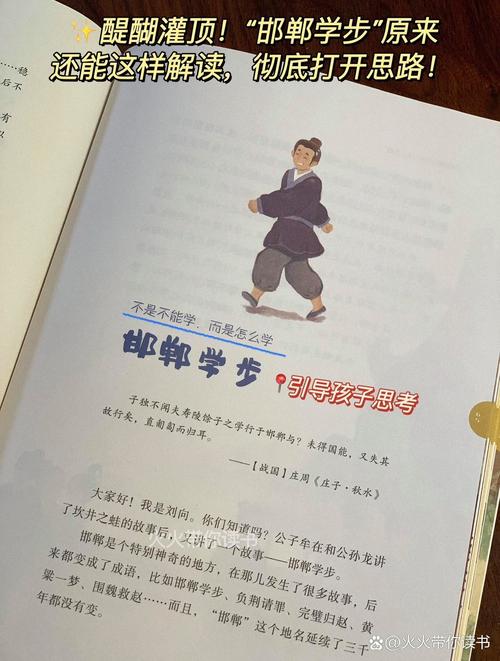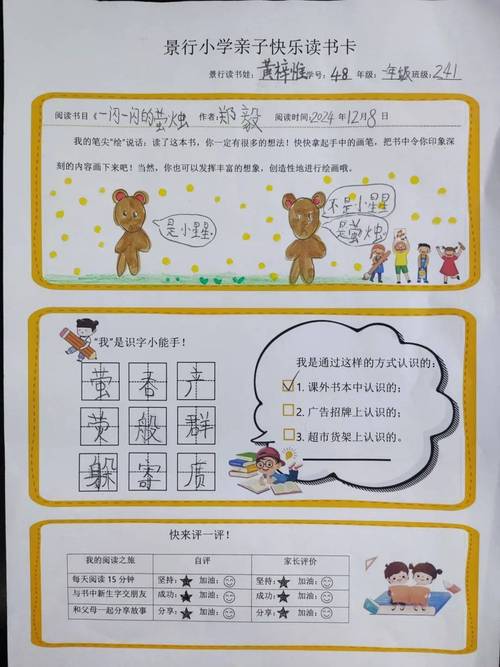在中国诗歌史上,"酒"与"诗"的结合在盛唐时期达到了空前绝后的艺术高度,而李白正是这种文化现象的集大成者,这位被后世尊称为"诗仙"的文人,用他充满酒香的笔墨,在《全唐诗》中留下了超过两百首与酒相关的诗作,当我们翻开这些泛黄的诗卷,不仅能看到一个嗜酒文人的率真性情,更能透过诗中的杯盏,触摸到整个盛唐时期士人阶层的文化脉搏。
酒香浸润的创作轨迹 李白的饮酒诗创作贯穿其生命始终,不同时期的作品呈现出迥异的精神特质,青年时期的《襄阳歌》中"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以夸张的笔法展现初入世事的豪迈;中年所作的《将进酒》"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则在狂放中透露出怀才不遇的苦闷;晚年在《月下独酌》里写下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已然呈现出阅尽沧桑后的孤寂况味,这种创作轨迹的演变,恰如陈年的酒浆,随着时光流转而愈发醇厚深沉。
细究其诗作中的酒器意象,可见其用词之精妙。《行路难》中的"金樽清酒斗十千"与《客中作》里的"玉碗盛来琥珀光",金银玉质的酒具折射出盛唐的物质繁华;而《金陵酒肆留别》中"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的市井酒肆,又展现出世俗生活的烟火气息,这种雅俗交融的审美取向,正是盛唐文化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酒意构筑的诗学空间 在李白笔下,酒不仅是现实中的饮品,更是构建诗意世界的重要媒介。《把酒问月》中"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的哲学追问,《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的超然意境,都将饮酒升华为精神对话的载体,这种以酒为媒的创作手法,突破了传统咏物诗的局限,开创出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
酒与自然意象的融合更显精妙。《月下独酌》中"花间一壶酒"的闲适,《游洞庭湖》"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的奇幻,都将饮酒行为置于天地自然的大背景中,这种天人合一的审美体验,既承袭了魏晋名士的遗风,又注入了盛唐人特有的浪漫气质,据统计,李白现存诗作中涉及自然景观的饮酒诗达87首,约占其饮酒诗总数的40%,足见这种创作倾向的自觉性。
酒魂映照的时代精神 李白的饮酒诗之所以能超越个人抒怀的范畴,关键在于其承载着特定的时代文化密码,在《少年行》"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的描写里,西域酒肆与胡姬形象的出现,映射出丝绸之路带来的文化交融;《客中作》"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的豁达,则折射出盛唐文人四海为家的精神特质,这些诗作犹如多棱镜,从不同侧面映照出开元天宝年间的社会风貌。
与同时代诗人相比,李白的饮酒诗呈现出独特的价值取向,杜甫笔下"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更多现实困顿,王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侧重离情别绪,而李白则创造出"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文化人格,这种将饮酒提升到生命哲学层面的创作实践,使他的诗作成为盛唐气象最生动的注脚。
酒道传承的文化基因 李白饮酒诗的影响力早已超越文学范畴,渗透到中华文化的深层结构,宋代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的化用,明代唐寅"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的摹写,乃至现代诗人余光中"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的礼赞,都可见李白诗酒精神的千年回响,这种文化基因的传承,使得"李白斗酒诗百篇"不再是个体记忆,而成为民族集体的审美共识。
从文化人类学视角观察,李白的饮酒诗实际上构建了中国文人的精神仪式,诗中的酒宴不再局限于物质享受,而是演变为身份认同的文化符号,无论是"烹羊宰牛且为乐"的狂欢,还是"我醉欲眠卿且去"的洒脱,都在反复确认着文人群体特有的价值观念和生活美学,这种文化范式的确立,对后世文人饮酒风尚产生了深远影响。
当我们细数李白诗中的酒香墨韵,看到的不仅是某个文人的创作偏好,更是整个时代的精神图谱,从《将进酒》的黄河之水到《金陵酒肆》的柳絮春风,从《月下独酌》的孤寂身影到《襄阳歌》的狂放笑颜,这些沾满酒渍的诗篇,最终酿成了中华文化最醇厚的精神佳酿,在当下这个物质丰裕而精神焦虑的时代,重读李白的饮酒诗,或许能让我们在古老的文字中,重新发现那份属于东方文人的生命智慧与审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