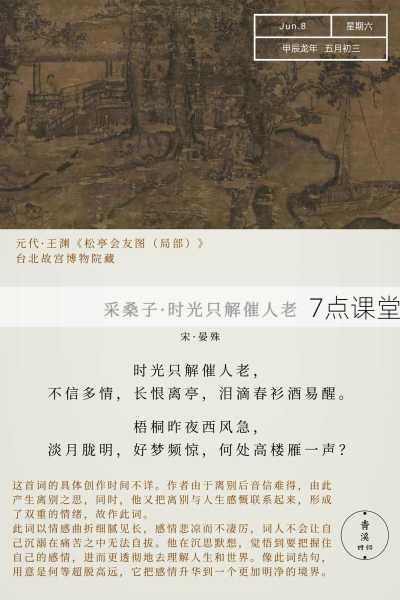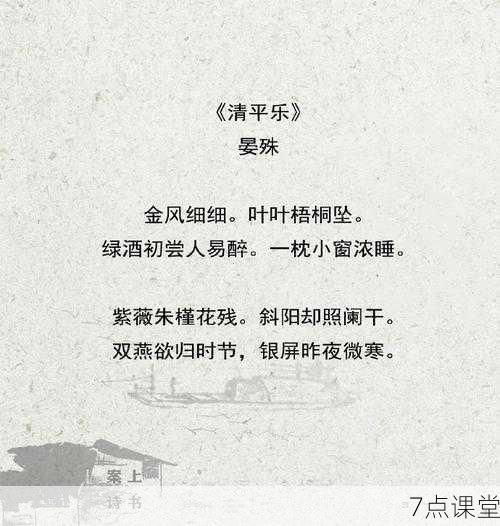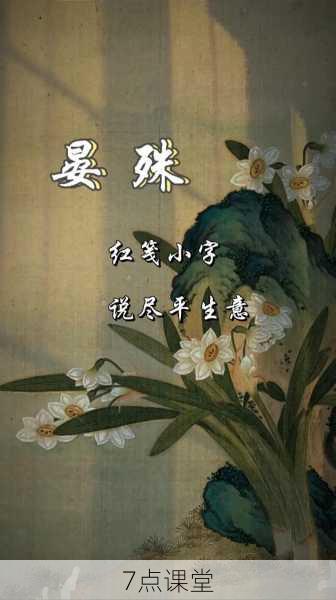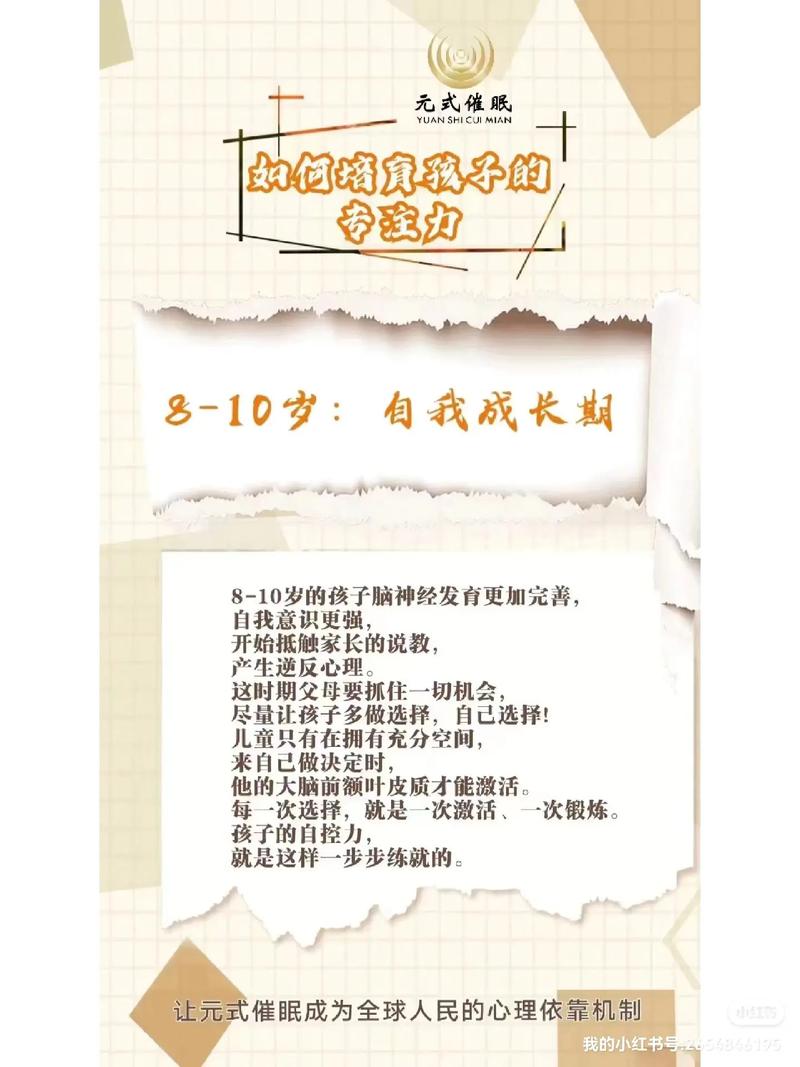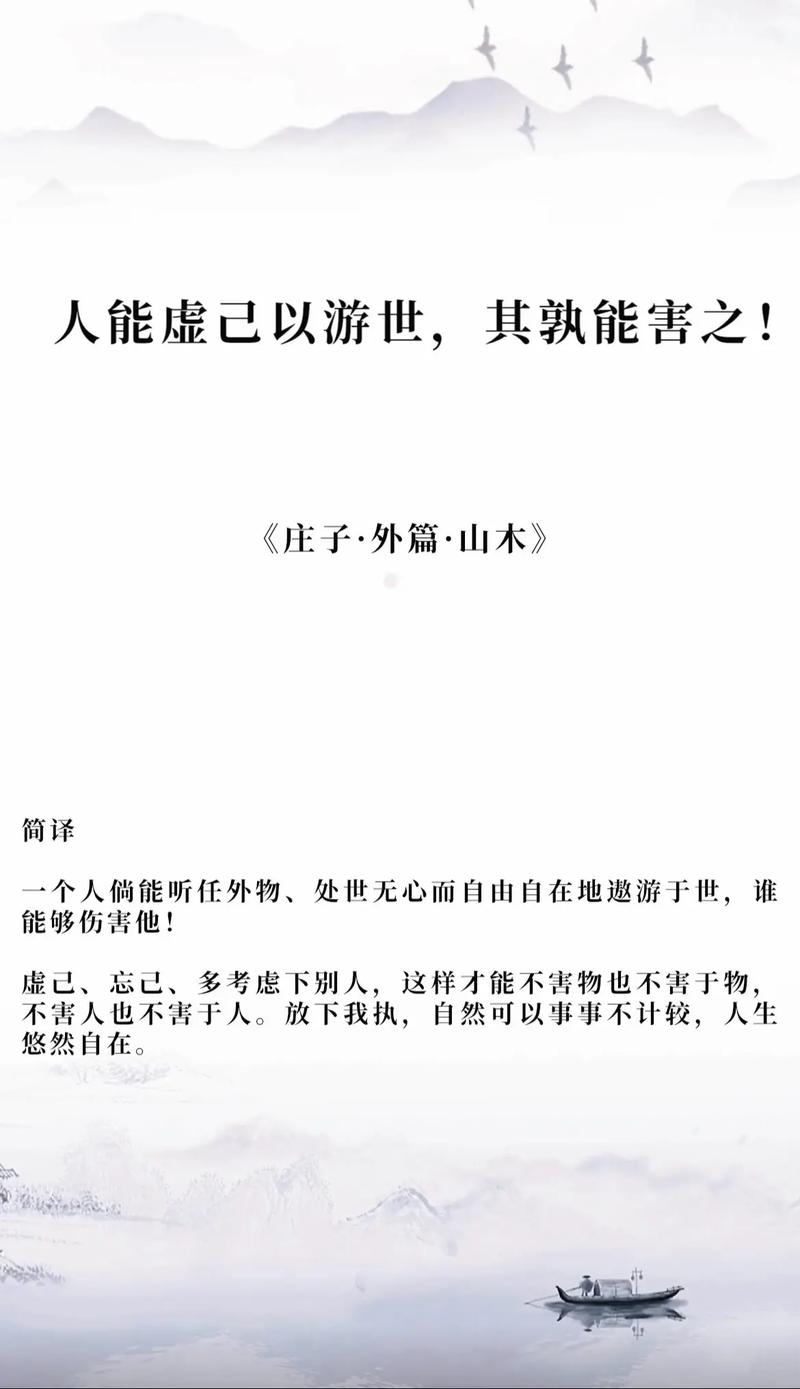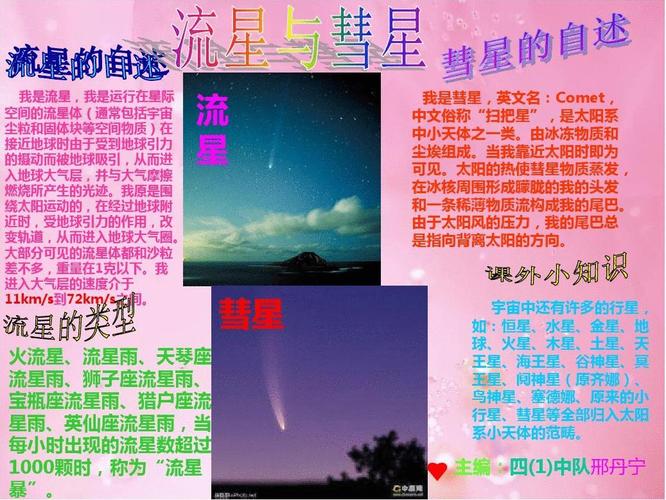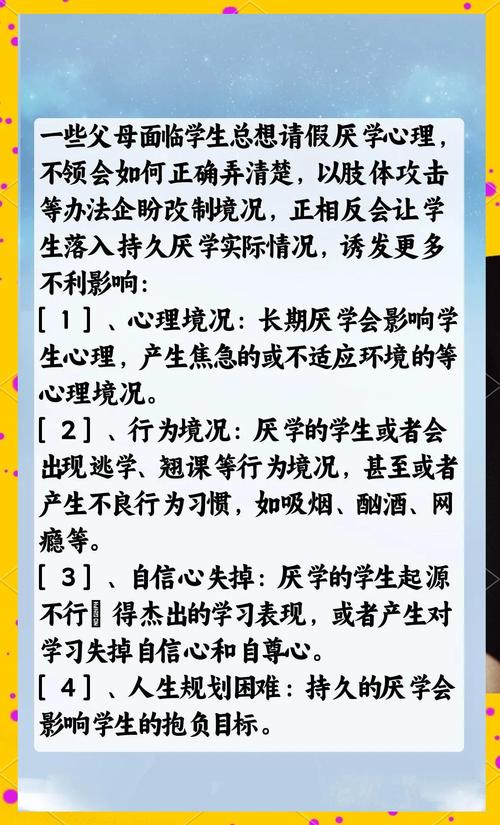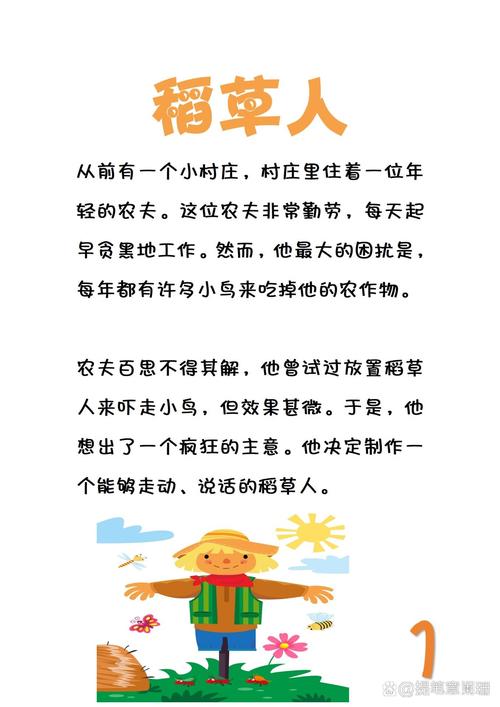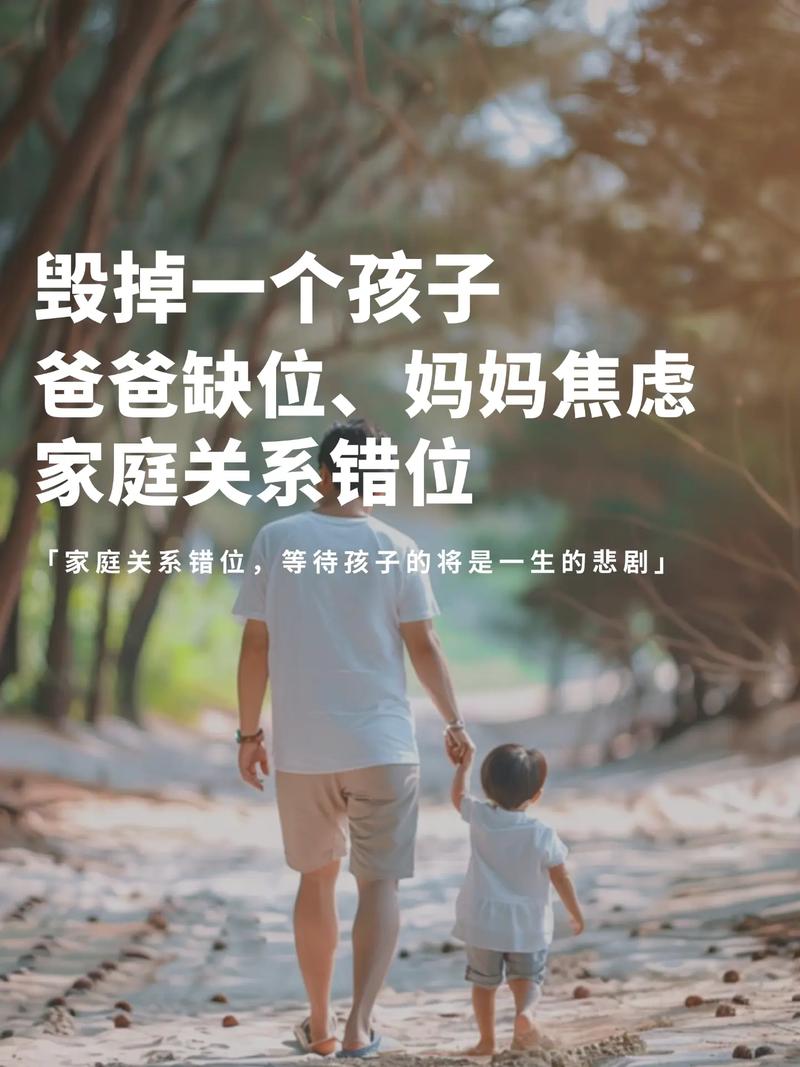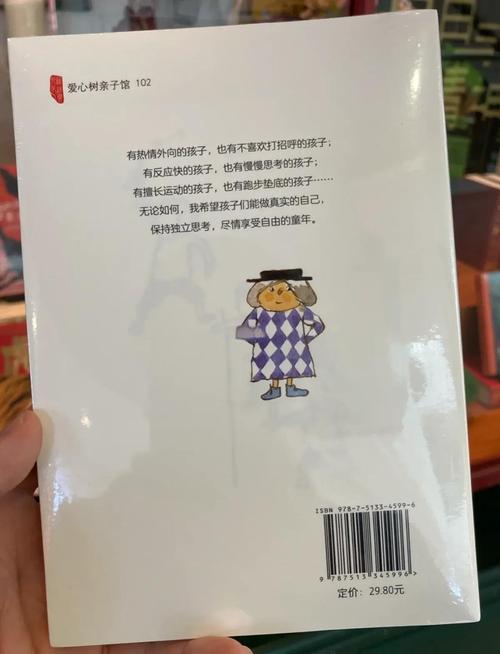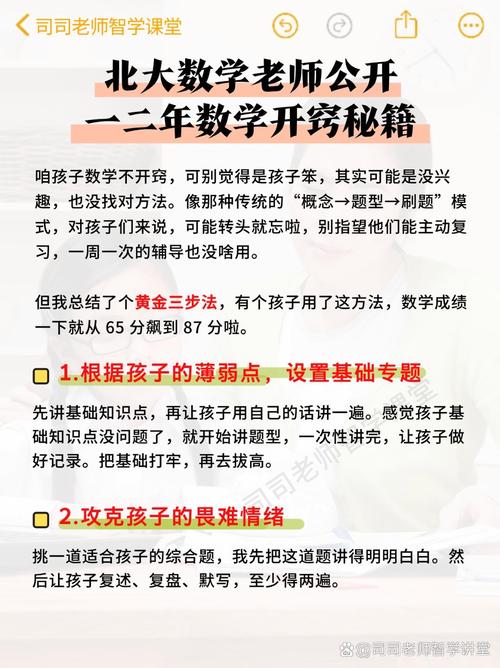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晏殊以其婉约清丽的词作闻名于世;在北宋政治舞台上,这位"宰相词人"又以实干家的身份参与国家治理,当我们深入探究这位历史人物的多重身份时,一个核心问题浮现眼前:晏殊究竟是否担任过宰相?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实则牵动着对宋代政治制度、文人从政传统以及个人命运的多维度解读。
晏殊的仕途轨迹与相位之谜 晏殊(991-1055),字同叔,江西临川人,少年得志的典范,景德二年(1005年),十四岁的晏殊以神童身份应举,被宋真宗赐同进士出身,开启了他长达五十余年的仕宦生涯,其官职升迁路径清晰可循:从秘书省正字起步,历任太常寺奉礼郎、光禄寺丞、太子舍人等职,至天禧二年(1018年)任翰林学士,已进入权力核心圈。
真正触及相位的时间节点在庆历三年(1043年)。《宋史·晏殊传》明确记载:"拜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兼枢密使",宋代实行"二府三司"制,其中同平章事即为实质宰相,但需注意的是,宋代宰相制度复杂,有使相、平章军国重事等不同名目,晏殊所任同平章事虽无"昭文馆大学士"之首席头衔,但确属宰执集团核心成员,主政期间主导了多项重大改革。
文人与政治家的双重修炼 晏殊的成长轨迹堪称宋代文官制度的典范模板,他在秘书省长达十二年的任职经历,不仅培养出深厚的文学修养,更在编修典籍、起草诏令的过程中深刻理解国家运作机制,这种特殊的成长路径,造就了其政治智慧与文学造诣的完美融合。
作为教育家的晏殊,在应天府书院重建过程中展现出超前眼光,他力主"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延请范仲淹等名师任教,推行分斋教学法,将书院打造成为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摇篮,这种教育改革思维,与其后来推行的政治革新一脉相承。
在治国实践中,晏殊展现出文人所罕见的务实精神,他主持修订《天圣编敕》,规范司法体系;整顿江淮漕运,保障京城物资供应;改革科举制度,增加策论比重,这些举措都体现着"经世致用"的施政特点。
宰相任上的政治遗产 庆历新政时期,晏殊作为宰相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他既支持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主张,又主张渐进式变革,在《论范仲淹等宣抚四路》奏疏中提出"事当有渐,改之不可暴"的稳健策略,这种改革思路虽遭激进派诟病,却有效避免了朝局剧烈动荡。
在人才举荐方面,晏殊堪称伯乐典范,欧阳修、富弼、韩琦等庆历名臣皆出其门下,王安石年轻时亦得其赏识,这种识人用人之明,源自他对士人精神特质的深刻理解,其《珠玉词》中"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哲思,正暗合其政治生涯中"新旧交替"的用人艺术。
对外交策略的把握尤见功力,面对西夏战事,他主张"以守为攻";处理宋辽关系时强调"守信修睦",这种稳健的外交方针,为北宋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期,其词作中"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意境,恰似执政者审时度势的全局视野。
文学创作与政治生涯的互文关系 晏殊词作中的政治隐喻值得玩味。《浣溪沙》中"满目山河空念远"的苍茫,暗含对边疆局势的关切;《蝶恋花》里"罗幕轻寒"的意象,或可解读为对朝堂风云的隐忧,这种将政治体验转化为艺术表达的能力,使其作品超越普通婉约词的格局。
执政理念在文学作品中的投射更为明显,其词中反复出现的"闲雅""从容"之境,恰与其"持重守成"的施政风格相呼应。《破阵子》中"巧笑东邻女伴,采桑径里逢迎"的田园描绘,折射出对民生安乐的追求,这种文学与政治的内在统一,构成独特的审美政治学。
文人集团的形成更显其政治智慧,通过西昆体诗派的引领、应天书院的经营,晏殊成功构建起跨越文学与政治的精英网络,这种以文会友、以政聚才的方式,深刻影响着北宋中期的政治生态。
历史镜鉴与当代启示 重新审视晏殊的宰相身份,对理解宋代政治具有特殊意义,他证明文人不仅能胜任宰辅之职,更能将文学思维转化为治国智慧,这种"文人治国"模式的成功,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政治文化遗产。
对现代教育的启示尤为深刻,晏殊案例表明,通识教育培养的复合型人才更具发展潜力,其兼顾文学修养与经世能力的成长路径,恰与现代"STEAM"教育理念异曲同工,当前教育改革中强调的"学科融合""跨界思维",都能在晏殊身上找到历史原型。
在文化传承层面,晏殊现象提示我们重新思考"文人从政"的现代价值,当技术官僚成为主流时,晏殊式的文化底蕴与政治智慧,依然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素质,其将人文关怀注入政治实践的经验,对当代政治文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晏殊是否当过宰相的追问,最终导向对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深度认知,这位"太平宰相"用一生诠释了"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理想,其文学创作与政治实践互为表里,共同构建起立体的人生境界,在当代语境下重读晏殊,不仅是对历史真相的考辨,更是对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再思考,当我们在古籍中寻找晏殊的足迹时,看到的不仅是一位宰相或词人,更是一个时代文化政治生态的鲜活样本,这种跨越千年的对话,将继续启迪着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