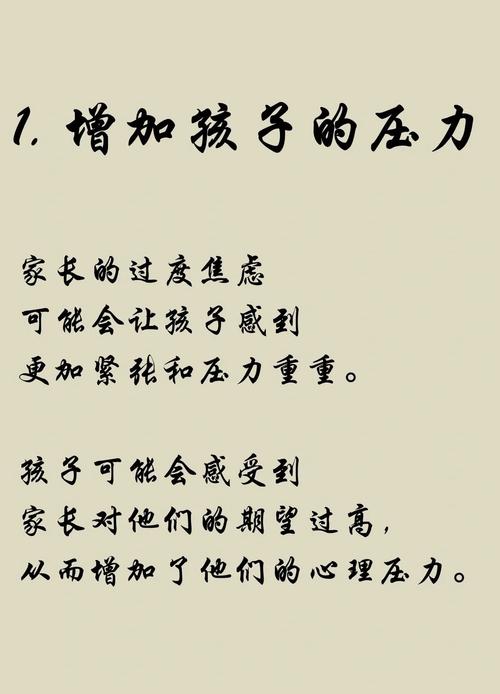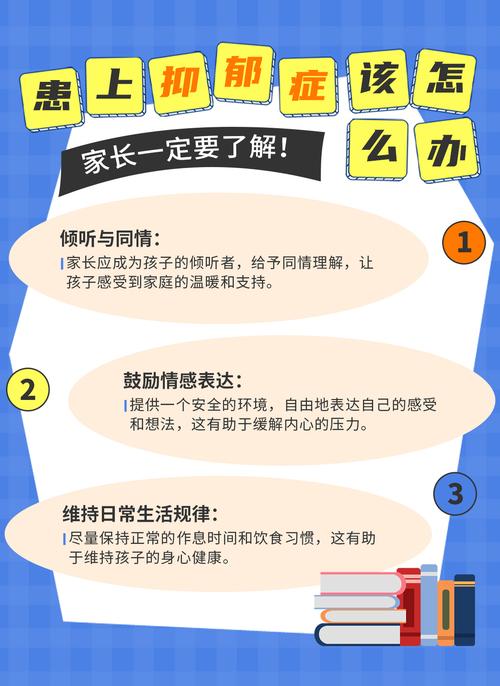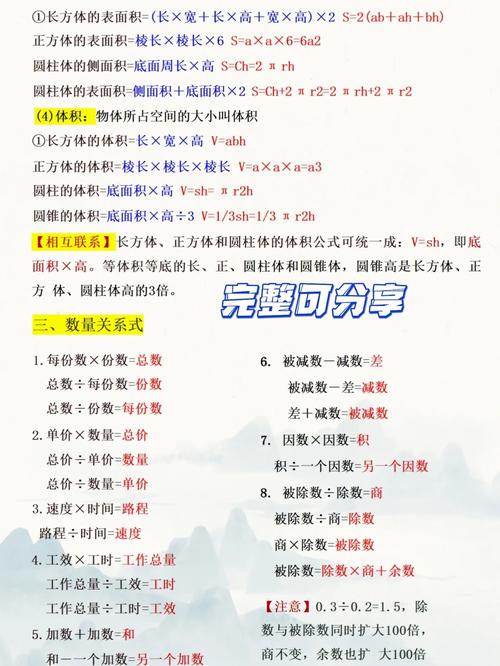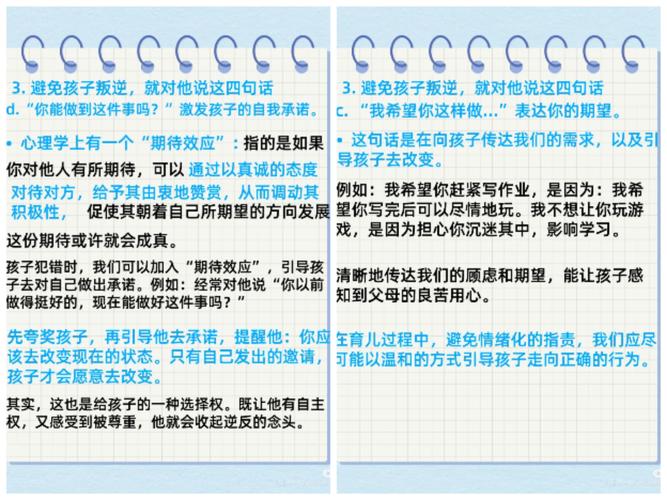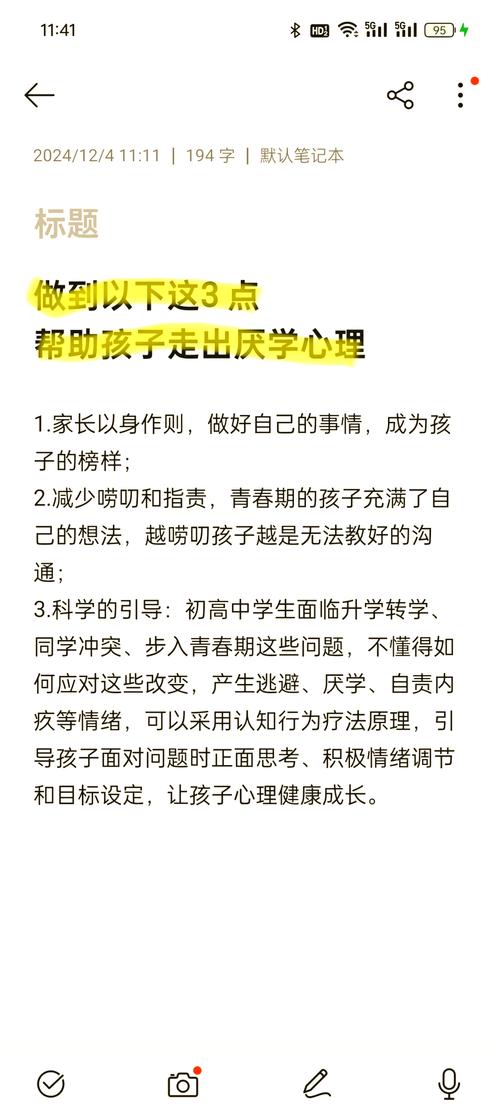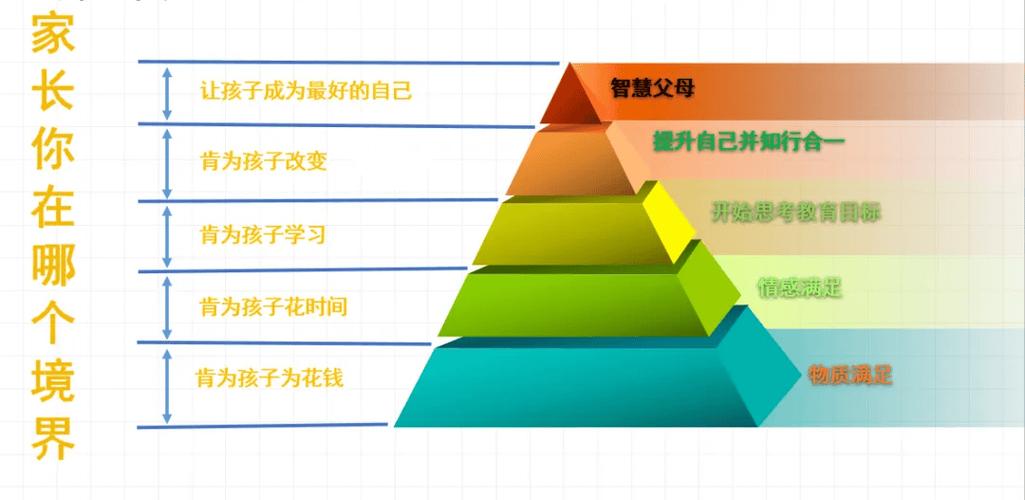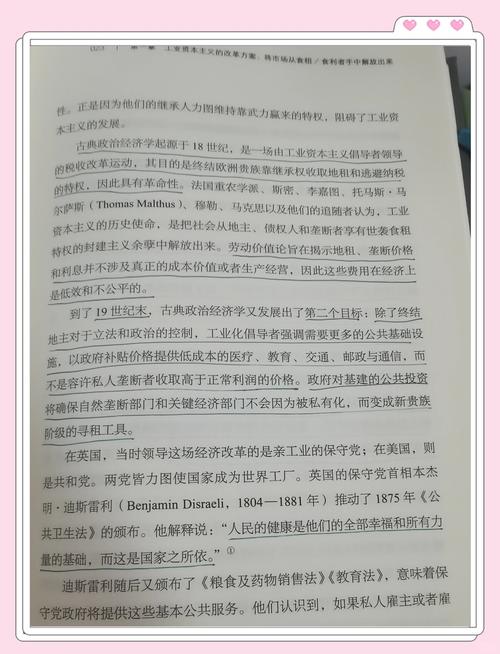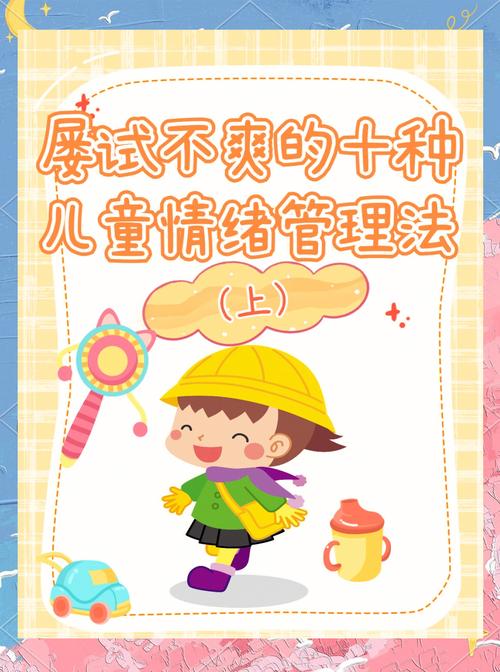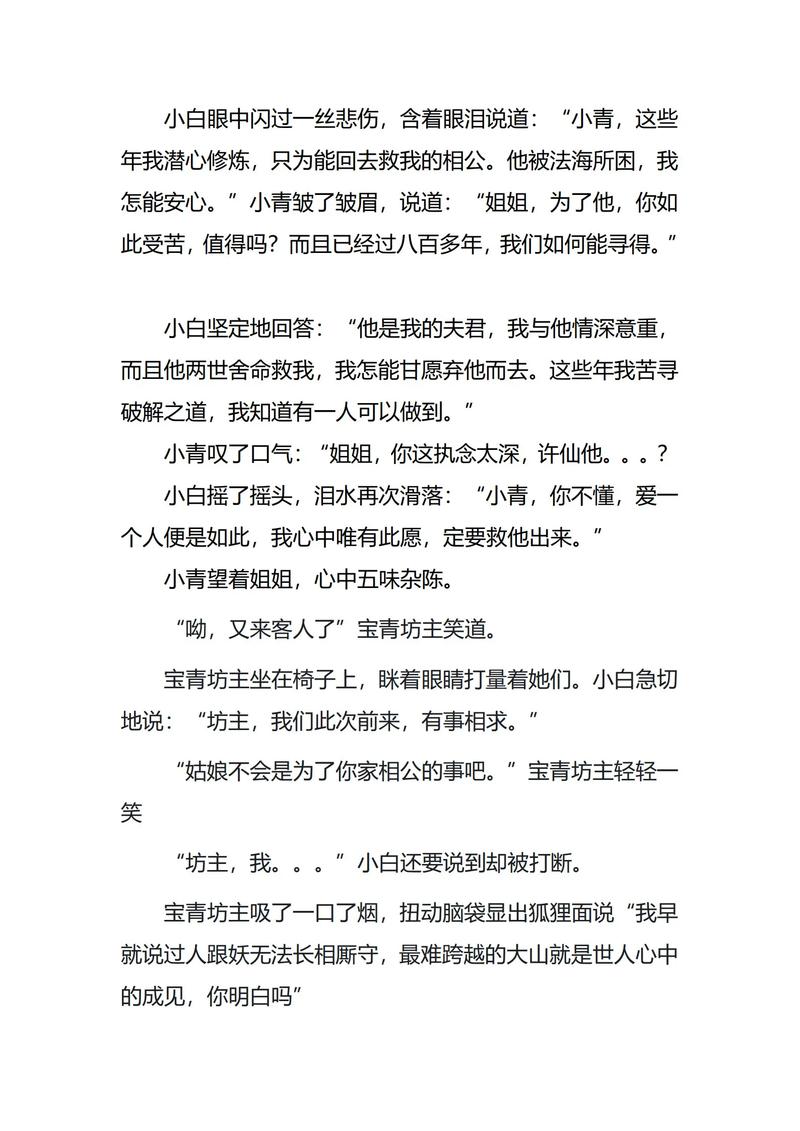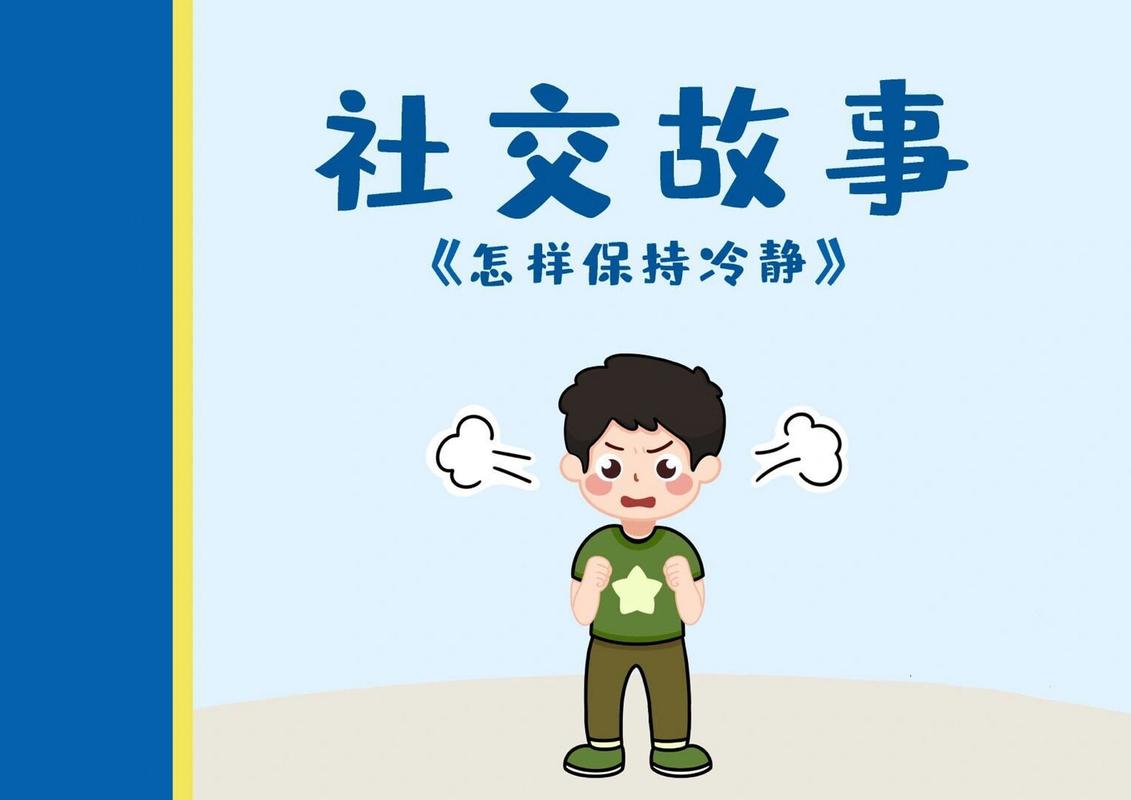千年诗坛的独特坐标 在中国诗歌史上,白居易(772-846)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社会影响力,在盛唐与中唐的转折期树立了醒目的文化坐标,这位跨越八、九世纪的诗人,不仅留下了三千余首传世诗作,更以"诗魔"与"诗王"的双重称号,在文学史长河中激荡出独特的文化回响,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称谓,恰如其分地勾勒出白居易作为文人的双重面向:既有对诗歌艺术的极致追求,又怀揣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诗魔"称谓的炼成之路
-
苦吟诗人的创作执着 "酒狂又引诗魔发,日午悲吟到日西"——白居易在《醉吟》中的自况,生动揭示了"诗魔"称号的由来,这种创作痴迷贯穿其整个艺术生涯:早年作《赋得古原草送别》时"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的勤勉;贬谪江州期间"二十年间,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的坚持;乃至晚年编纂《白氏长庆集》时"家藏金帛,而筐笥中唯留文集"的执着,都印证着他对诗歌创作的魔性痴迷。
-
语言艺术的革新突破 白居易突破盛唐诗歌的典雅范式,开创"老妪能解"的通俗诗风,其《新乐府》五十首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翁》)的平白如话,"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心理刻画,实现了诗歌语言从庙堂到市井的跨越,这种对传统诗歌语言的"入魔式"革新,使他的作品真正走入民间,形成"禁省、观寺、邮候墙壁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的传播奇观。
"诗王"桂冠的现实根基
-
诗歌创作的量化突破 作为唐代存诗数量最多的诗人,白居易的创作不仅体现在质量上,更表现在惊人的创作量上,其《白氏长庆集》收诗2914首,远超李白(约1000首)、杜甫(1400余首)的存世作品,这种高产并非简单的数量堆积,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生活的全方位观察之上,从宫廷宴饮到田家劳作,从边塞烽火到市井百态,形成唐代社会的全景式诗史。
-
讽喻诗派的开创实践 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的"新乐府运动",将诗歌创作提升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高度。《秦中吟》十首中"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尖锐批判,《杜陵叟》中"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的农民控诉,都展现出诗人作为"诗王"的社会担当,这种创作理念直接影响了宋代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现实主义诗风。
双重身份的辩证统一
-
艺术追求与社会责任的交融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这种文学主张在其创作实践中得到完美体现:《长恨歌》既展现"回眸一笑百媚生"的艺术魅力,又暗含"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历史反思;《琵琶行》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乐描写中,寄寓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社会悲悯。
-
文人理想与官僚身份的和解 作为仕途显达的诗人(最高任刑部尚书),白居易成功调和了士大夫的政治抱负与文人情怀,任杭州刺史时修筑西湖堤岸(今白堤),既造福百姓,又催生"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的隽永诗句;晚年任太子少傅期间创作《池上篇》,在"勿言不深广,但取幽人适"的闲适背后,仍保持着"心中为念农桑苦"的人文关怀。
文化基因的现代启示
-
雅俗共赏的创作智慧 白居易"不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的创作理念,对当代文化传播具有重要启示,其作品跨越千年仍被选入中小学教材,证明真正伟大的艺术既能承载深刻思想,又能实现大众传播,这种平衡雅俗的智慧,恰是当下文艺创作值得借鉴的宝贵经验。
-
文以载道的永恒价值 在娱乐至上的当代语境中,白居易"唯歌生民病"的创作精神更显珍贵,他教导我们:真正的文化影响力,不仅在于艺术形式的创新,更在于对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怀,这种将个人才情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文化品格,正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
双重光环下的文化镜像 当我们重新审视"诗魔"与"诗王"这两个历史标签,看到的不仅是个体诗人的成就,更是中国文化中"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价值统一,白居易用毕生实践证明:真正的艺术大师,既能沉醉于语言魔力的创造,又能肩负起时代良知的重量,这种双重文化身份的构建,不仅成就了诗人的历史地位,更为后世树立了文人精神的典范,在当下多元文化碰撞的语境中,白居易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传诵千年的诗句,更是一面映照文化良知的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