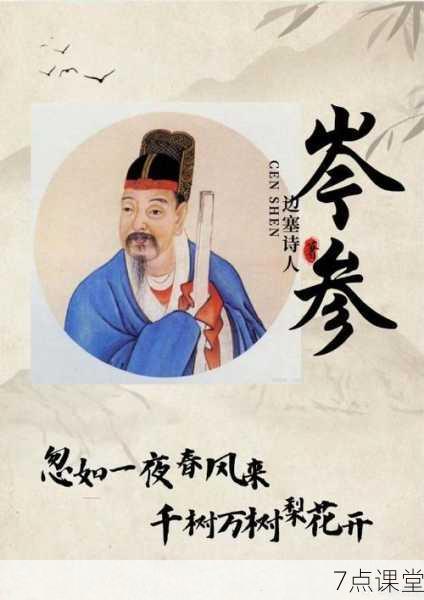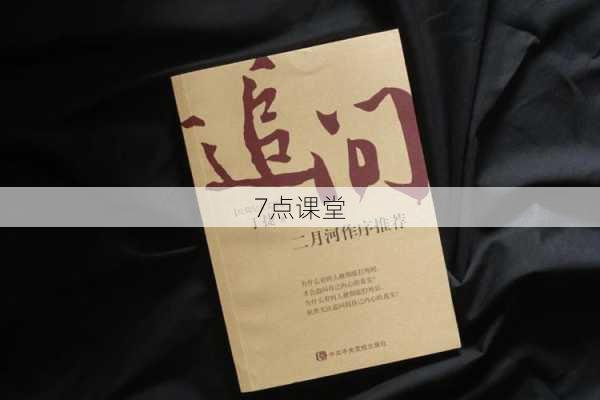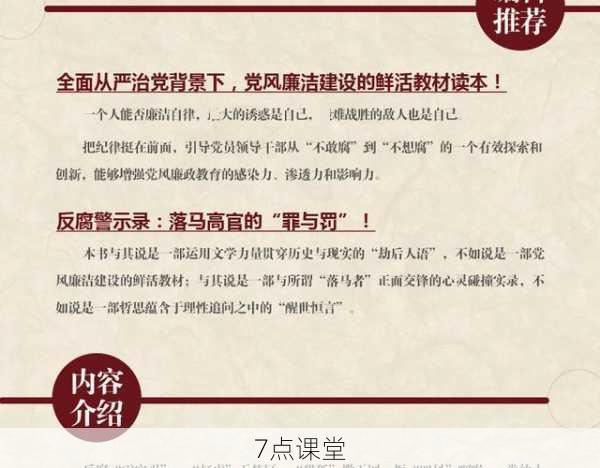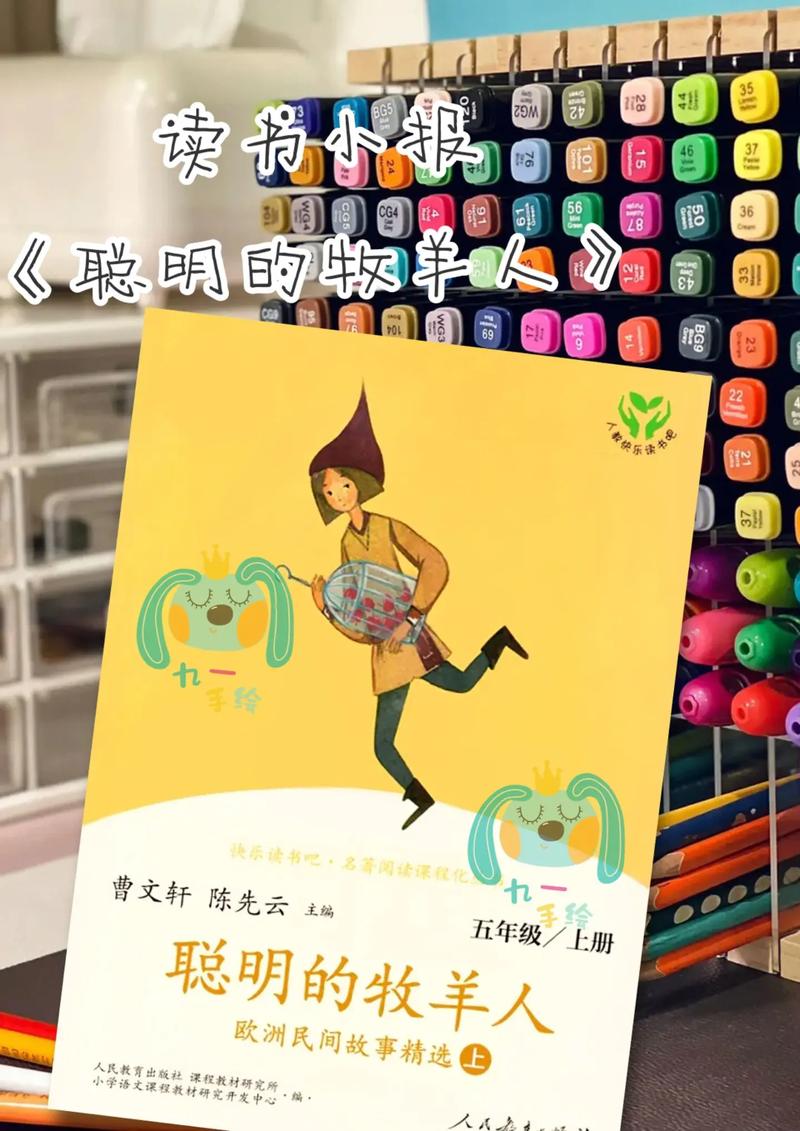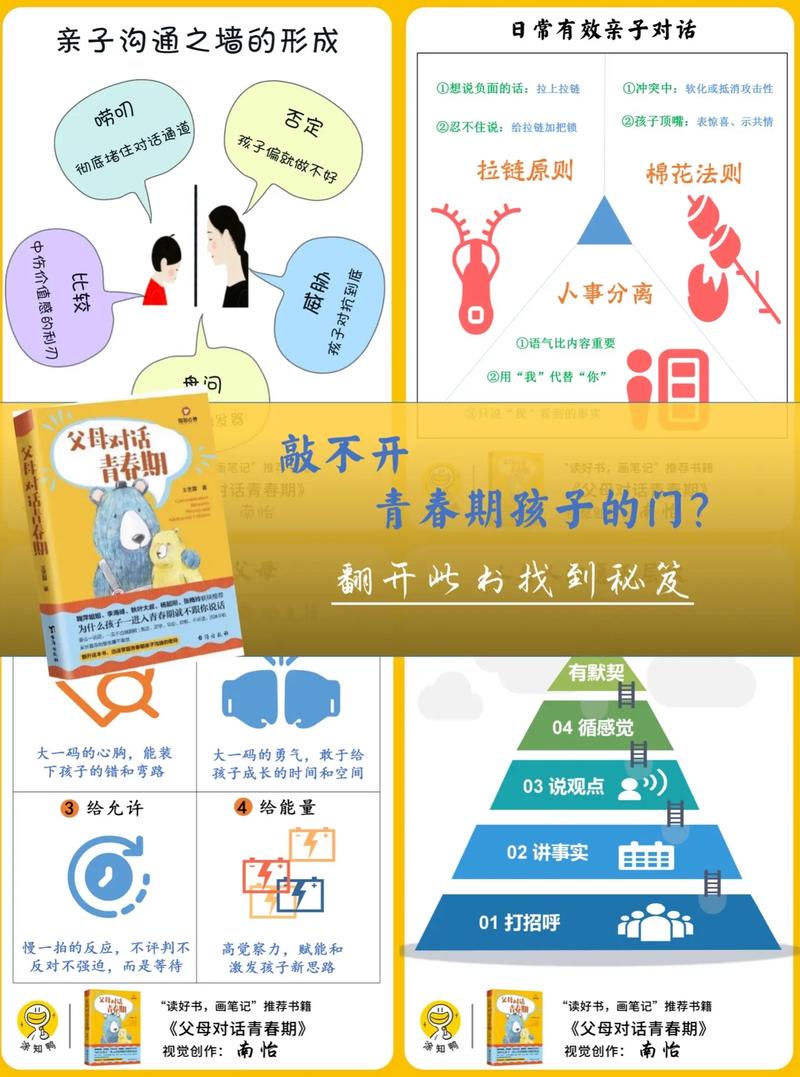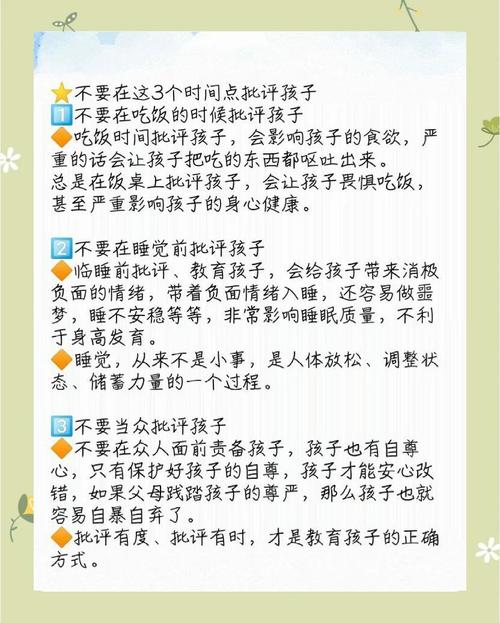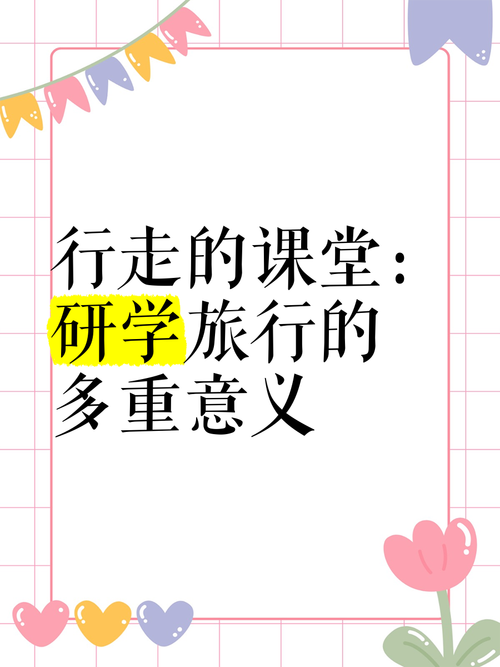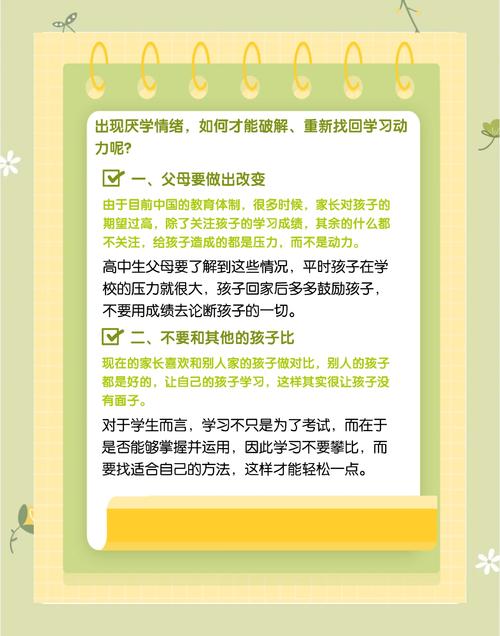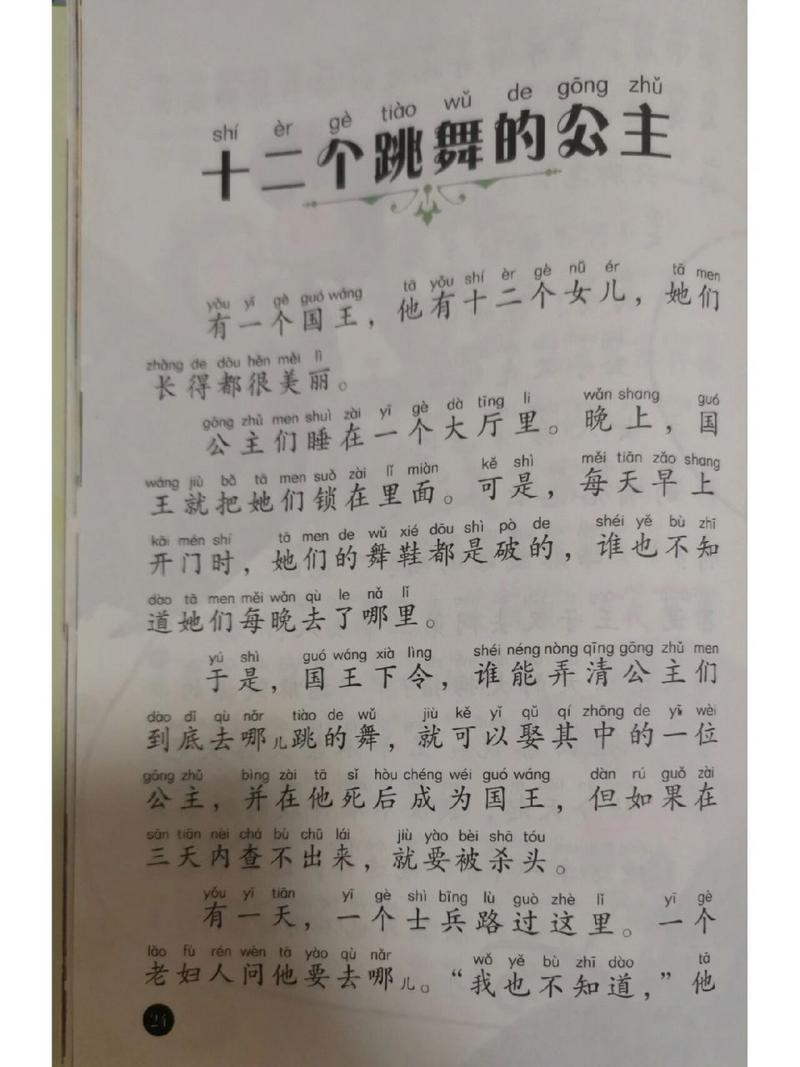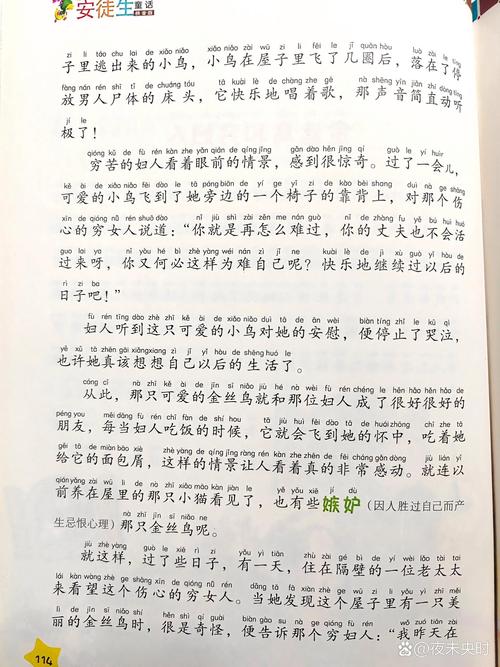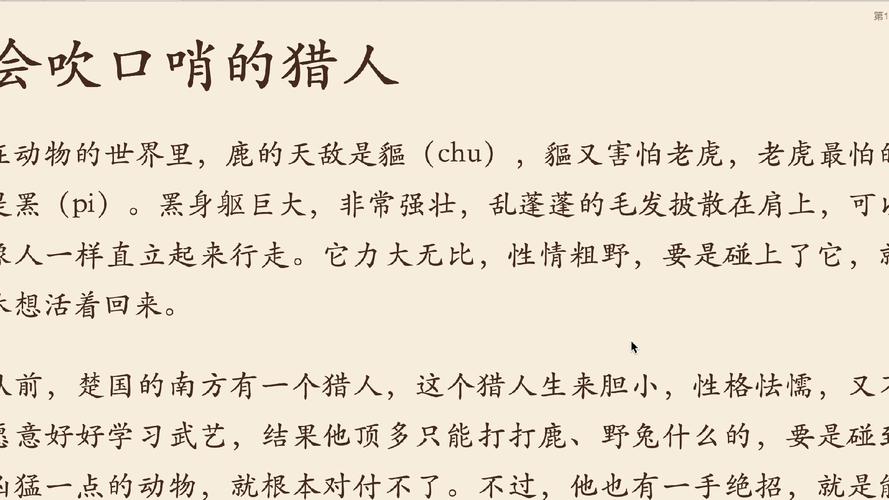历史迷雾中的身份探源 在中国文学史上,"岑氏双杰"的称谓曾引发学界长达数百年的讨论,岑勋与岑参的关系考证,不仅涉及唐代世族谱系的梳理,更关乎我们对盛唐文学传承脉络的深刻理解,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岑氏家族自南朝梁代迁居江陵,至唐代已形成显赫的文学世家,岑参在《感旧赋》中自述:"参,相门子,五岁读书,九岁属文",其曾祖父岑文本为太宗朝宰相,父亲岑植官至晋州刺史,这样的家族背景为理解岑氏文脉提供了重要线索。
岑勋的真实身份在《全唐文》中留有蛛丝马迹,天宝十一载(752年)的《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明确记载:"南阳岑勋撰,朝议郎判尚书武部员外郎琅琊颜真卿书,朝散大夫检校尚书都官郎中东海徐浩题额。"这段珍贵史料不仅证实了岑勋的文人身份,更揭示了其与颜真卿、徐浩等文化名流的交游网络,值得注意的是,岑参在《冀州客舍酒酣贻王绮》诗中提及"况值岑勋远相访",这为两人的交往提供了直接证据。
文学成就的平行比较 岑参作为边塞诗派的巅峰代表,其作品展现的不仅是个人才华,更是整个盛唐气象的浓缩。《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奇绝想象,《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里"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的壮阔意境,都已成为中国诗歌的经典意象,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深度融合的创作特征,恰与其"功名只向马上取"的人生追求相印证。
相较而言,岑勋的文学遗产则呈现出不同的面向,除《多宝塔碑》外,其现存作品虽数量有限,但在李白《将进酒》题注中"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的记载,暗示着与诗仙的密切交往,考《李太白全集》,现存与岑勋唱和的诗作达五首之多,送岑征君归鸣皋山》更透露出岑勋曾隐居修道的经历,这种隐逸与入世的双重特质,与岑参的边塞豪情形成鲜明对照。
历史误读的深层成因 关于二人关系的混淆,最早可追溯至明代胡震亨《唐音癸签》,该书将岑勋误作岑参从弟,这个错误被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沿袭,导致后世诸多误解,这种误判的形成,既源于古代文献传抄的讹误,也折射出文学史书写中的"大家遮蔽"现象——次要文人的生平考订往往让位于主流大家的学术关注。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世族联姻的复杂性,岑氏家族在唐代通过婚姻与颜氏、徐氏等大族结盟,这种盘根错节的姻亲关系,使得"岑勋"在不同文献中时而被称为"南阳岑勋",时而又冠以"江陵岑氏"的郡望,加之唐代文人习惯以郡望相称,更增加了后世考辨的难度。
正确认知的学术价值 澄清岑勋与岑参的真实关系,对于理解盛唐文学生态具有多重意义,这有助于还原文学世家的传承机制:岑氏家族自岑文本至岑参,四代间涌现出岑羲、岑曼倩等十余位文人,这种持续的文化产出绝非偶然,而是世族教育体系与文学传统的共同结果,二人的交往网络折射出盛唐文人圈的流动特征,岑勋与李白、颜真卿的交游,岑参与高适、杜甫的唱和,共同织就了八世纪中叶的文化图谱。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考察,岑参的边塞书写与岑勋的中原交游,恰好构成唐代文人"出塞"与"入幕"两种典型生存状态的对照,这种差异不仅源于个人选择,更受到家族资源分配的影响——作为家族重点培养的对象,岑参得以通过科举入仕,而岑勋则更多依靠文学交游维持社会地位。
文化传承的现代启示 这个案例给予当代教育三点重要启示:其一,文学研究需要秉持"知人论世"的传统,将文本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解读;其二,家族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具有重要研究价值,魏晋至隋唐的世族文学传统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其三,对历史细节的严谨考辨,是避免文化误读的根本途径。
当我们重读岑参《逢入京使》中"故园东望路漫漫"的慨叹,或品味岑勋在《多宝塔碑》里"禅师建言,杂华献颂"的佛理阐释时,应当意识到:这些文字背后跃动的不只是个体生命,更是一个文化世家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这种对话的深层意义,正在于它展现了中华文明传承中个体与家族、文学与历史的永恒互动。
(全文共1287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