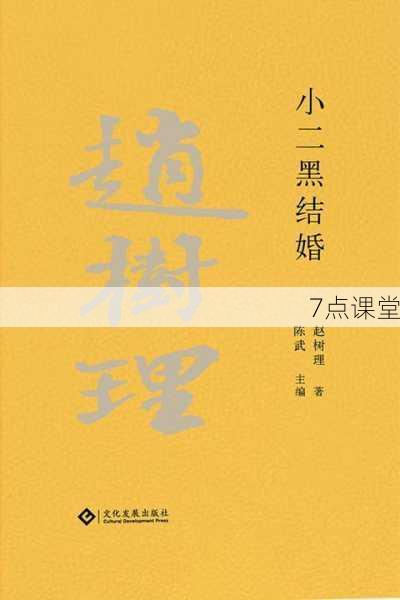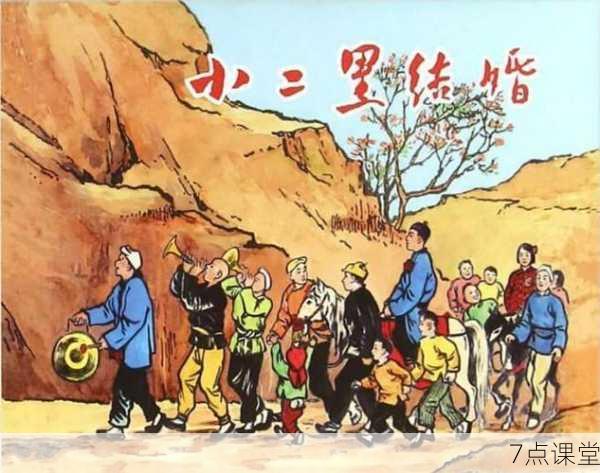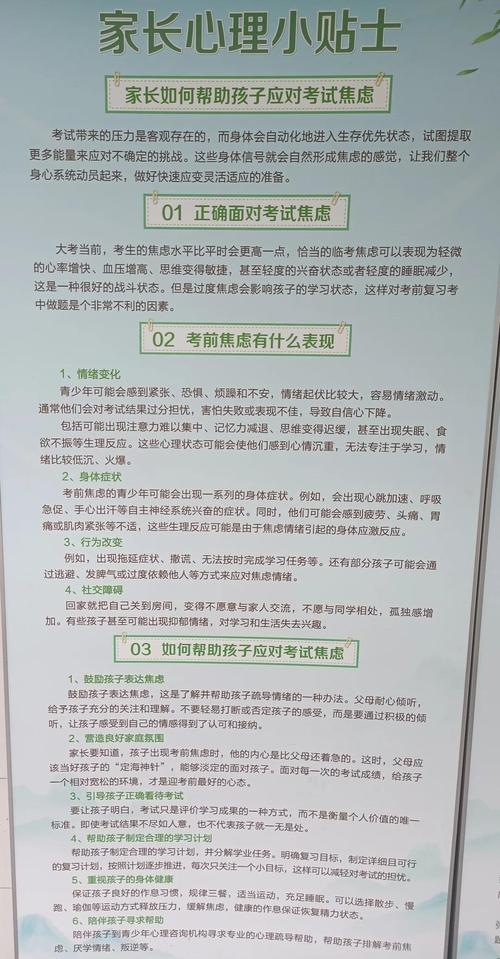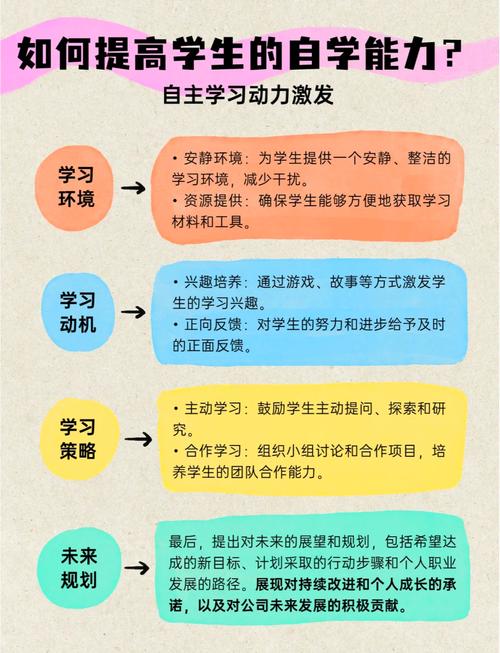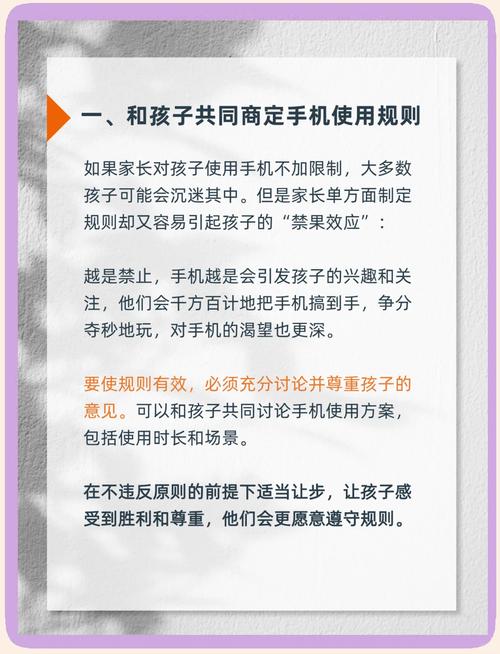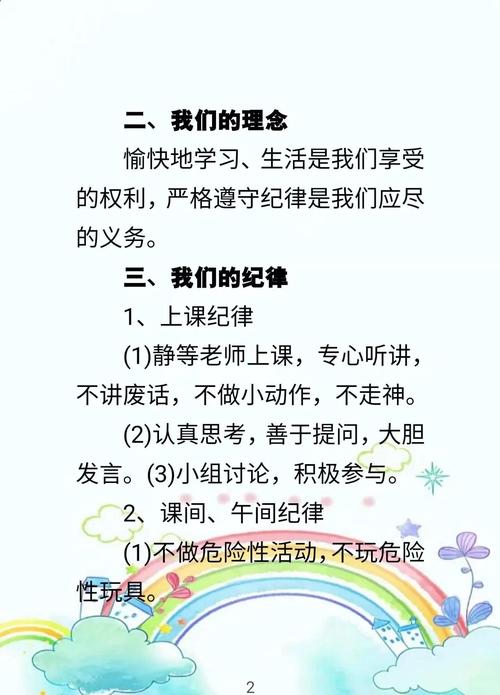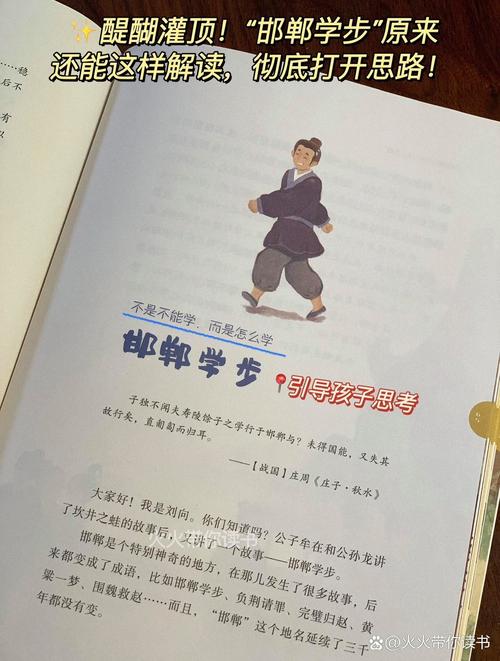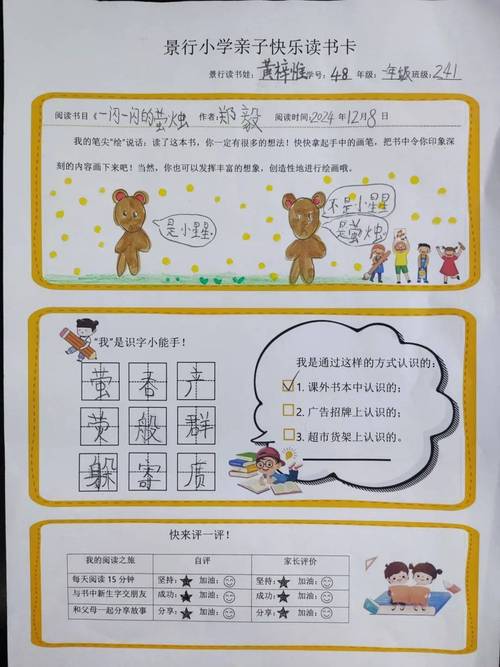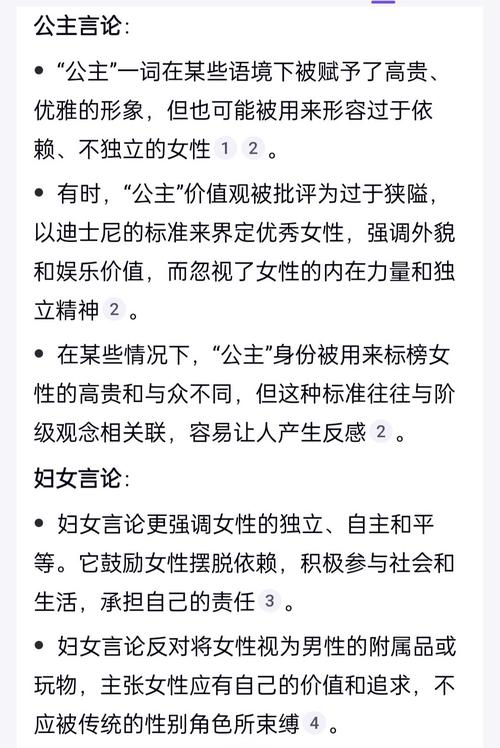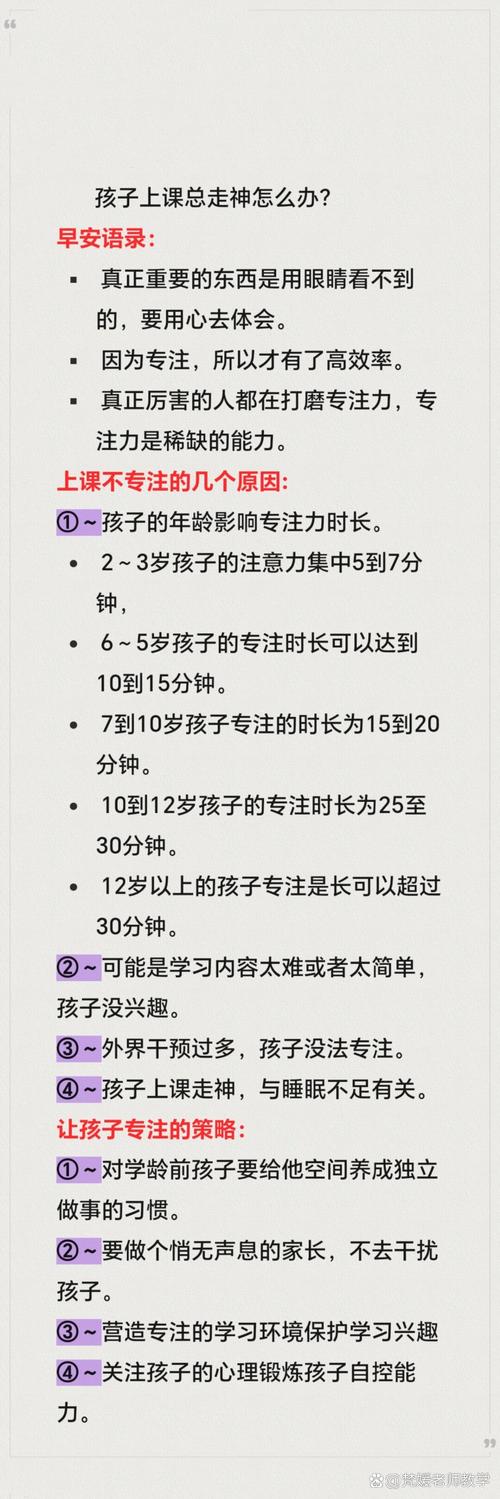在政治与民俗的交界处
1943年秋,太行山区的一盏煤油灯下,赵树理用毛笔在麻纸上写下《小二黑结婚》的最后一章,这部仅三万字的中篇小说,以"解放区第一部婚姻自主题材作品"的标签横空出世,却在其表层叙事之下埋藏着更为深邃的文化密码,当我们以当代视角重新审视这部乡土文学经典,会发现它不仅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宣传文本,更是一部重塑民间话语体系的文化实验作品。
双重解构:对传统叙事的颠覆
(一)婚恋秩序的解构与重构 小说开篇即以"不宜栽种"的荒诞故事,将二诸葛的封建家长形象推至前台,这个熟读《玉匣记》的乡村知识分子,与三仙姑的"米烂了"形成镜像对照,共同构成旧式婚俗的守门人形象,而小二黑与小芹的私会场景,被刻意安排在传统禁忌的"打谷场"这一公共空间,实则暗含对隐秘情爱叙事的突破。
赵树理创造性地运用"斗争会"这一革命场景,将私人情感纠纷转化为公共政治事件,当金旺兄弟的诬告遭遇民主政府的理性审判,传统宗法制度下的"私了"机制被彻底瓦解,这种叙事策略既符合解放区政策宣传需要,又暗合民间对"青天大老爷"的集体想象。
(二)语言系统的民间转译 小说中"顶门事"、"打哈哈"等山西方言的运用,绝非简单的乡土气息点缀,赵树理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转化为可触摸的民间话语体系,政府布告中的"婚姻自主"政策,在文本中被具象为"两人商量着办"的日常对话,这种政治话语的民间转译,构建起意识形态传播的毛细血管网络。
文化狂欢:民间智慧的现代性转化
(一)诙谐美学的政治功能 三仙姑"老来俏"的装扮描写,实则是巴赫金狂欢理论的本土化实践,她那"镶边宽腿裤"与"绣花鞋"的滑稽形象,既是对封建礼教的形式反叛,又暗含对过度政治化的潜在消解,这种充满民间诙谐的叙事策略,使严肃的革命主题获得更广泛的传播可能。
(二)仪式空间的符号重构 小说中的"斗争会"场景具有双重象征意义:既是新政权确立权威的仪式空间,又是民间"看热闹"传统的延续,当三仙姑在会场羞愧难当,"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这个细节揭示出旧式民间信仰体系在公共政治场域中的自我消解过程。
教育启示:文本的跨时空对话
(一)文学教化的双重维度 《小二黑结婚》的传播史本身就是部生动的教育案例,据太行山革命纪念馆档案记载,仅1944年就有17个村剧团改编演出此剧,文盲农民通过观剧理解新政权的婚姻政策,这种"文学—戏剧—生活"的传播链条,创造出独特的文化教育模式。
(二)现代教育的反思镜像 当下乡村教育面临的传统文化断裂问题,在赵树理的文本中早有预警,二诸葛的"不宜栽种"与现代某些家长的盲目迷信形成跨时空呼应,提醒我们教育现代化不能割裂民间智慧根系,而小芹在斗争会上的自主陈词,则为当代青少年公民教育提供了历史注脚。
超越时代的文化密码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21世纪的乡村振兴战略,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展现的民间智慧转化能力依然具有启示价值,那个坚持要"按八字"办事的二诸葛,与今天某些乡村的彩礼之争形成微妙互文;三仙姑的"米烂了"故事,则在网络时代的谣言传播中找到新的变体。
这部诞生于战火中的小说,以其独特的叙事智慧证明:真正的民间文学从来不是政治宣传的传声筒,而是文化基因的活态传承,正如赵树理在创作谈中所言:"要把政策消化成山药蛋",这种将意识形态融入乡土肌理的创作理念,至今仍在叩问着每个教育工作者的文化自觉。
在太行山的褶皱里,《小二黑结婚》依然以它特有的质朴与狡黠,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教育的最高境界,或许就是将文明的曙光,编织进最本真的生活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