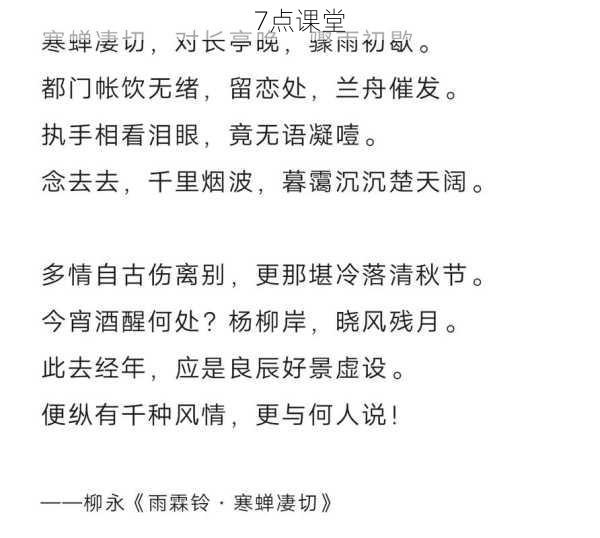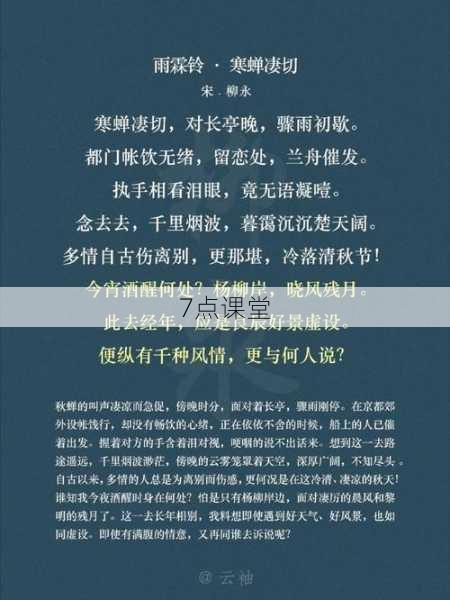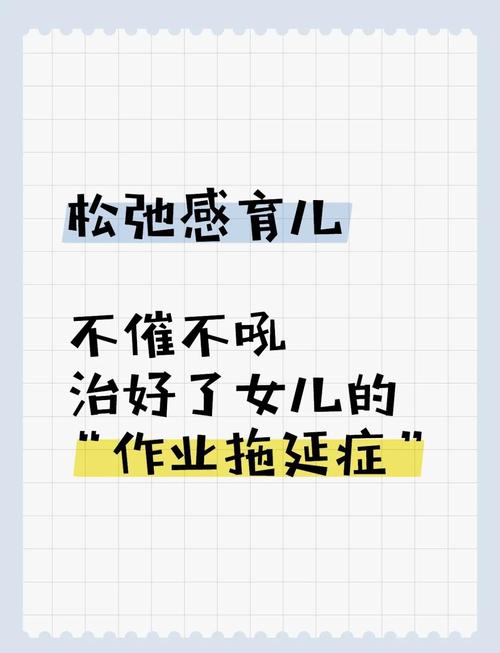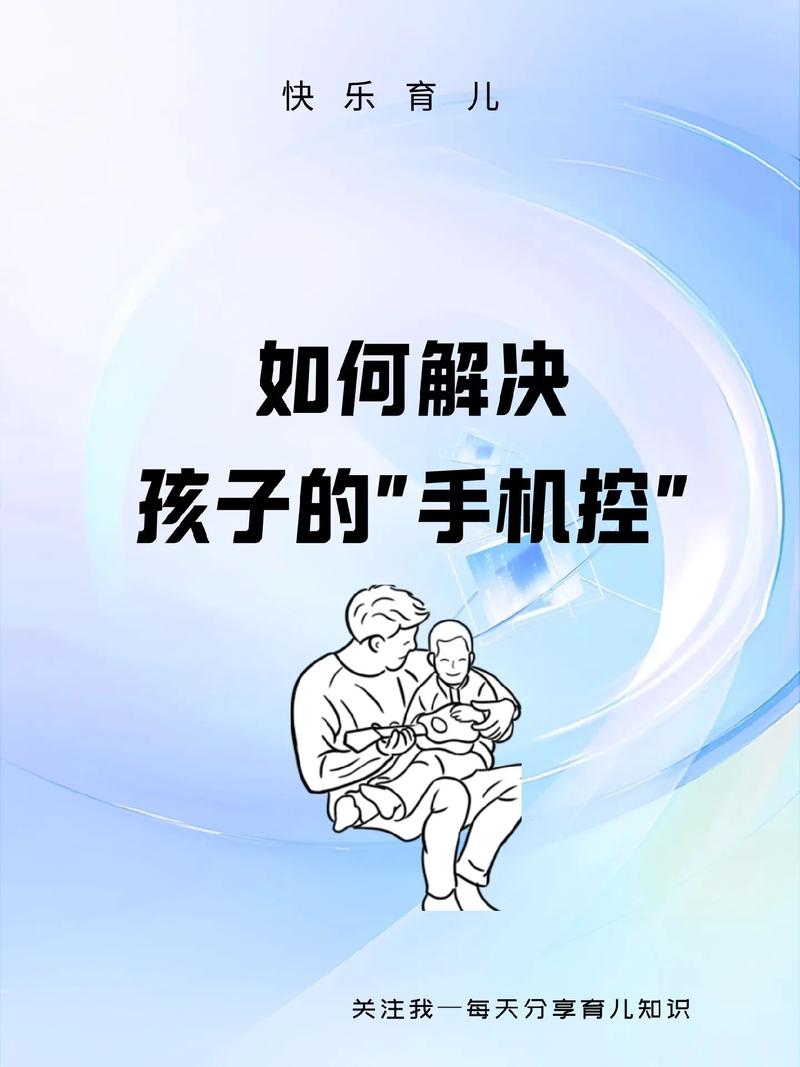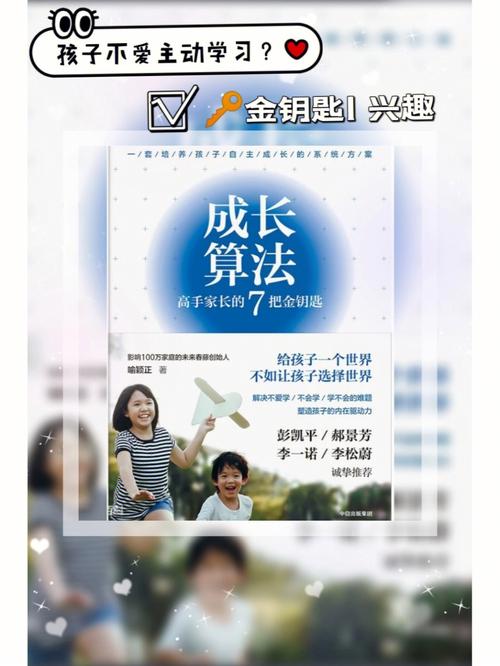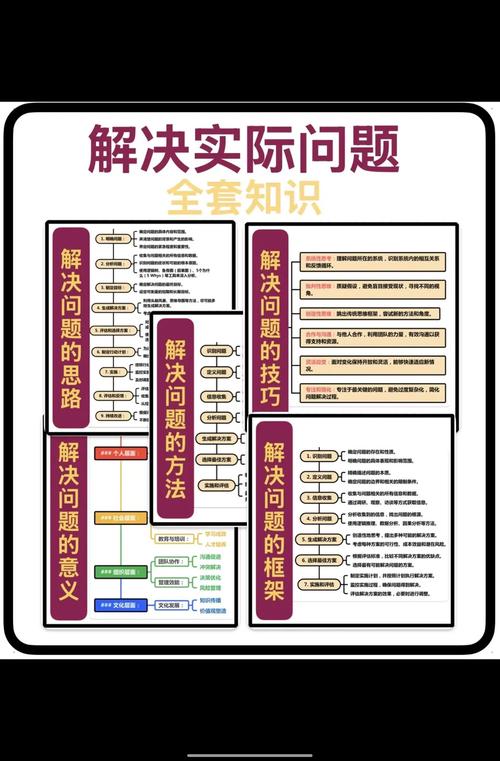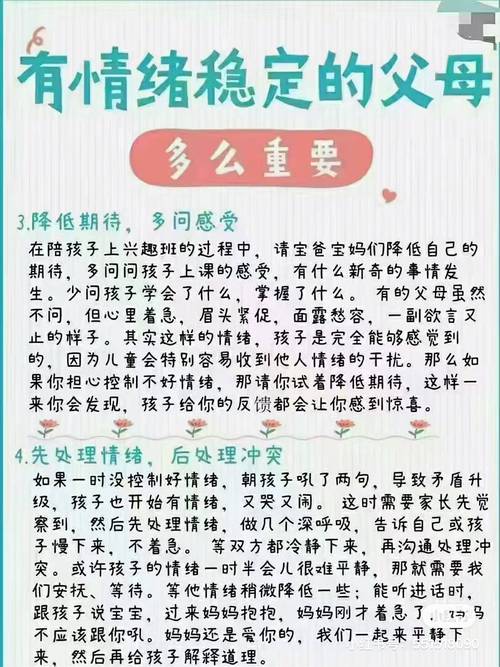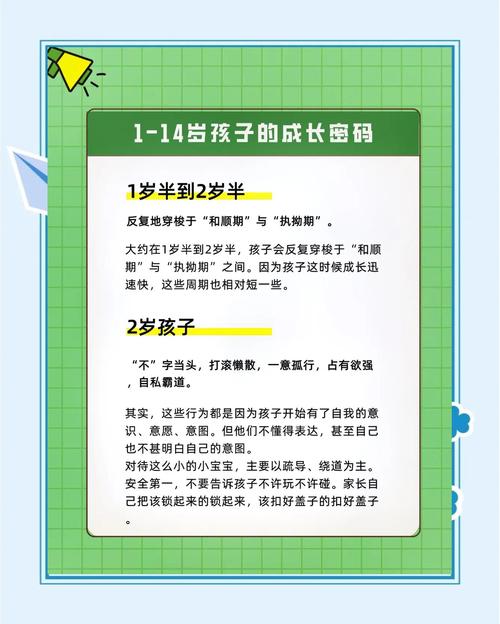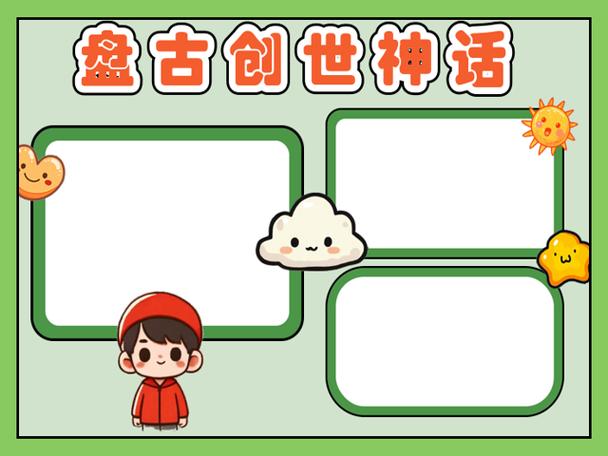历史帷幕下的贬谪真相
公元805年深秋,一叶扁舟载着三十三岁的柳宗元逆湘江而上,这位曾经的监察御史里行、礼部员外郎,此刻褪去了长安城里的紫袍玉带,以戴罪之身踏上永州这片瘴疠之地,这场看似突然的政治放逐,实则酝酿于中唐诡谲的政治漩涡之中。
永贞革新集团的崛起绝非偶然,安史之乱后的六十年间,宦官专政与藩镇割据已使唐王朝危如累卵,据《资治通鉴》记载,贞元末年,朝廷岁入不足天宝年间的四成,而藩镇截留的赋税高达七成,在此背景下,以王叔文为首的革新派提出"收宦官兵权、抑藩镇财权、选贤能官吏"三大主张,正切中时弊要害,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自述:"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可见其参与革新的初衷。
权力博弈中的牺牲者
永贞革新的失败本质上是一场新旧势力的生死较量,据《旧唐书·宦官传》记载,宦官集团掌握神策军达十五万之众,其经济实力更通过"宫市"等特权机构渗透到各个领域,当革新派试图收回宦官兵权时,俱文珍等大宦官立即联合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等藩镇势力反扑,这场政变的速度令人震惊:从唐顺宗被迫退位到革新派集体遭贬,仅相隔二十三日。
柳宗元的特殊身份加剧了其政治风险,作为河东柳氏子弟,他本属关陇贵族集团,却选择与寒门出身的王叔文结盟,这在门阀观念根深蒂固的唐代实为异数,其《封建论》中"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的主张,更直接触动了世族利益,当革新失败时,他自然成为各方势力集中打击的对象。
瘴疠之地的精神突围
永州十年塑造了独特的"贬谪文人"柳宗元,初至永州时"居是州,恒惴栗"的惶恐(《始得西山宴游记》),逐渐转化为对生命的深层思考,在冉溪畔,他效法屈子"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游南亭夜还叙志》);于法华寺西亭,写下"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的悟道之语,这种精神蜕变在《江雪》中达到极致,那个"独钓寒江雪"的蓑笠翁形象,正是诗人超越现实困境的艺术投射。
文学觉醒与思想新生
贬谪生涯意外催生了柳宗元的文学巅峰,永州期间创作的485篇诗文,占其现存作品的六成以上。《捕蛇者说》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呐喊,将批判现实主义推向新高度;《三戒》系列寓言开创了寓言文学独立成篇的先河;《天对》《天说》等哲学著作,更是构建起"元气自动"的唯物主义体系,这种创作转变印证了韩愈的评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
历史长河中的双重镜像
回望这场千年之前的政治风波,柳宗元的永州之贬折射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在《与李翰林建书》中,他自陈"罪恶滔天,无所容于天地之间",这种强烈的罪感意识,恰是儒家士大夫政治人格的深刻写照,但正是这种贬谪经历,使其突破了传统文人的价值框架,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提出"文以明道"的文学观,为宋代古文运动埋下伏笔。
当代教育者当从这段历史中获得启示:柳宗元在永州完成的精神涅槃证明,真正的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人格的锻造,他在《种树郭橐驼传》中阐述的"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教育理念,至今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当我们带领学生诵读《永州八记》时,不仅要赏析其"清莹秀澈,锵鸣金石"的文字之美,更要领悟一个知识分子如何在绝境中实现精神的超越与重生。
这场跨越千年的贬谪,最终演变为中国文化的幸事,柳宗元用十年的瘴烟蛮雨,酿就了中华文明史上一坛醇厚的思想佳酿,其人生轨迹印证着:真正的文人,即便被时代放逐,也终将在文化的长河中找到永恒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