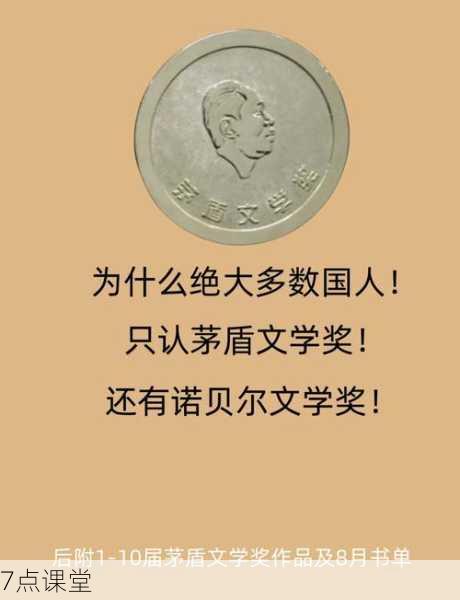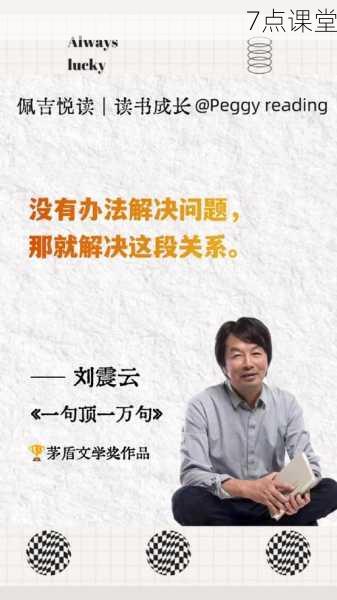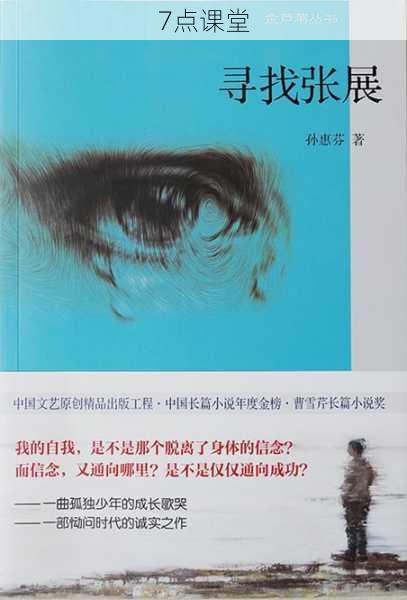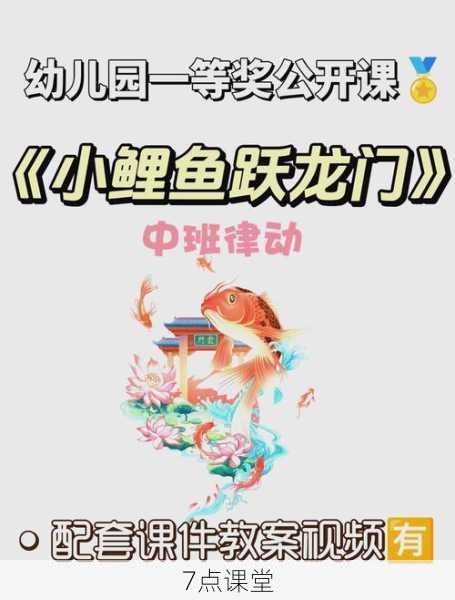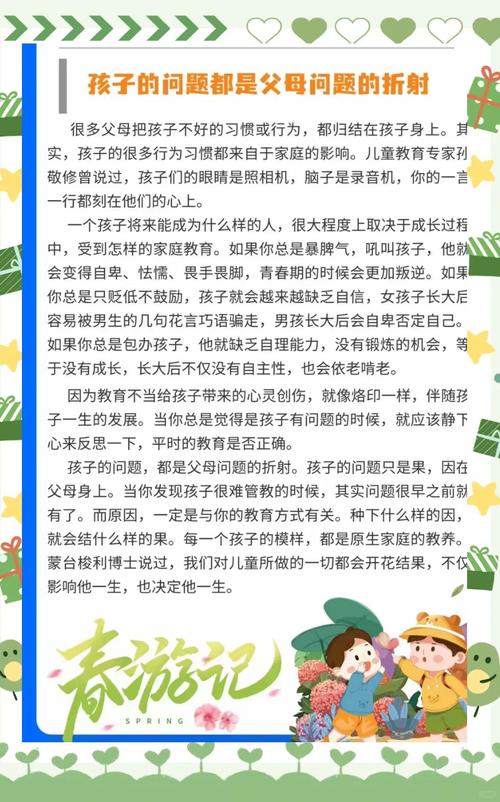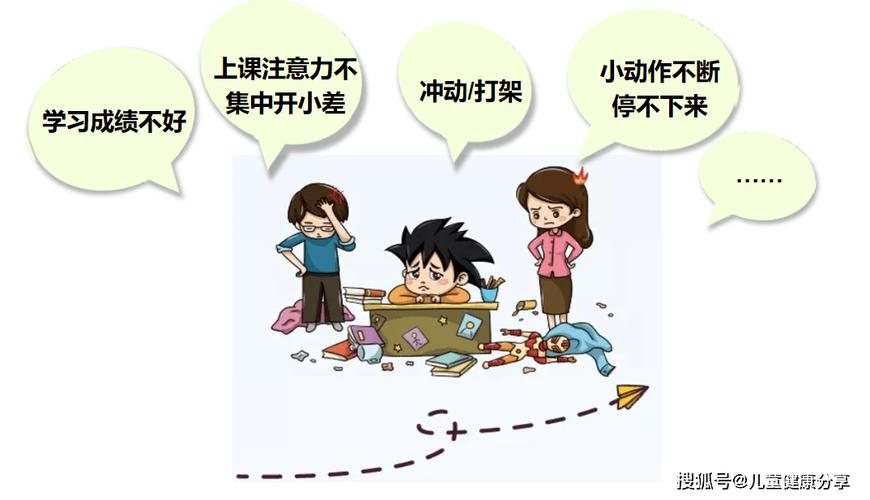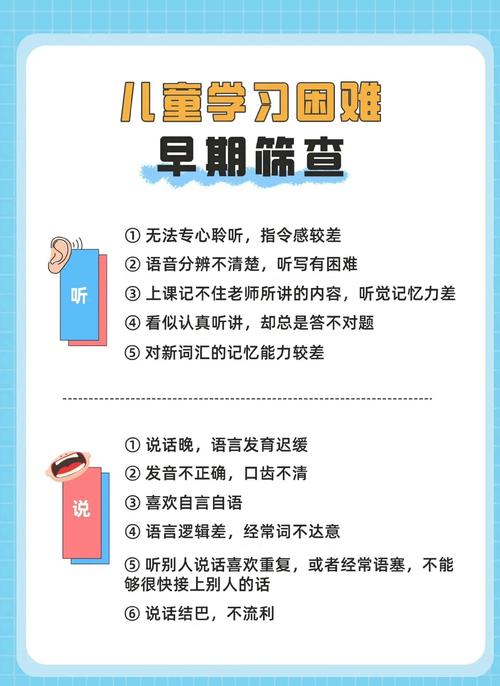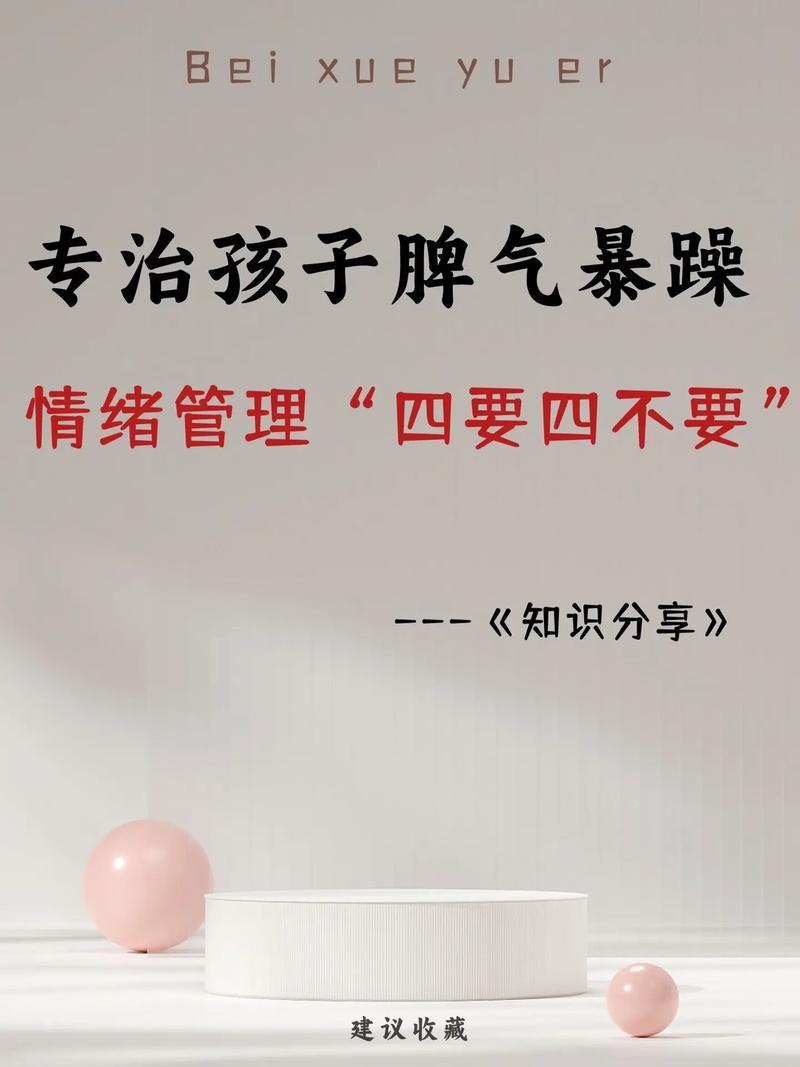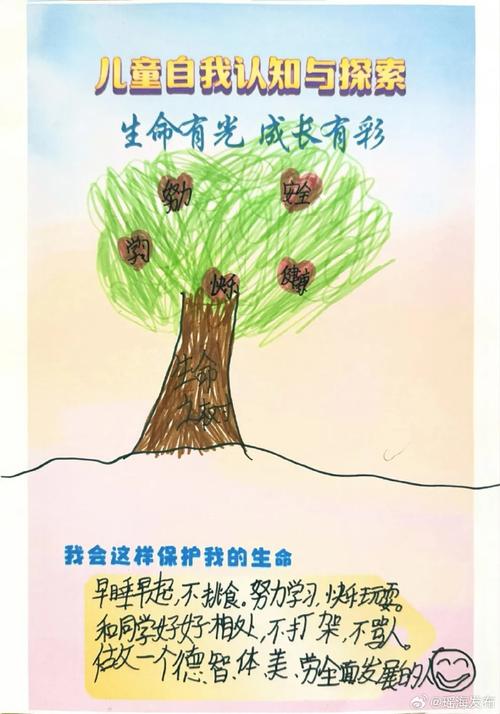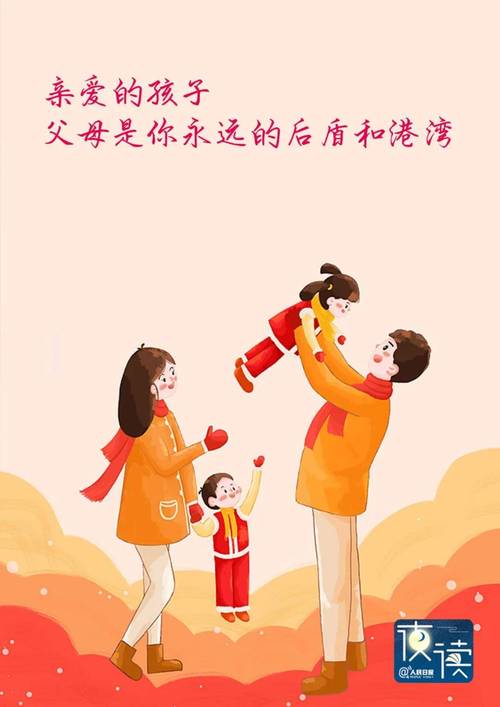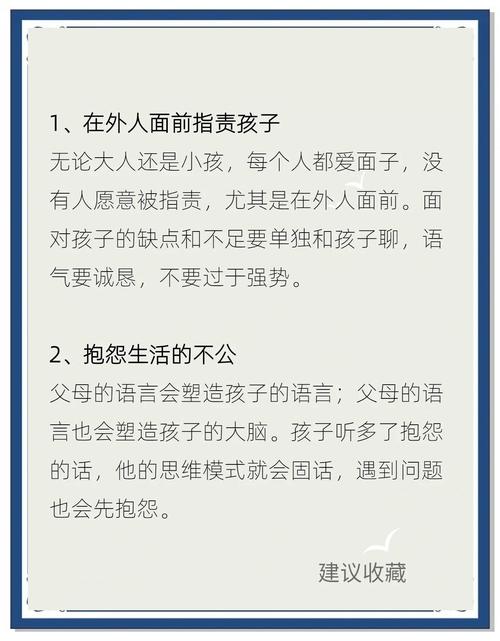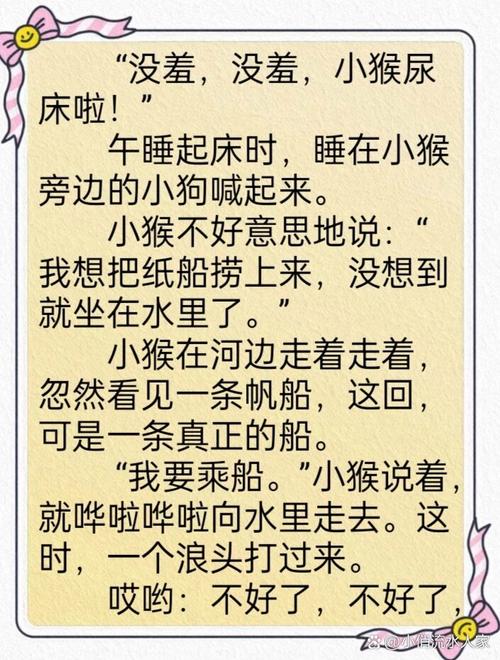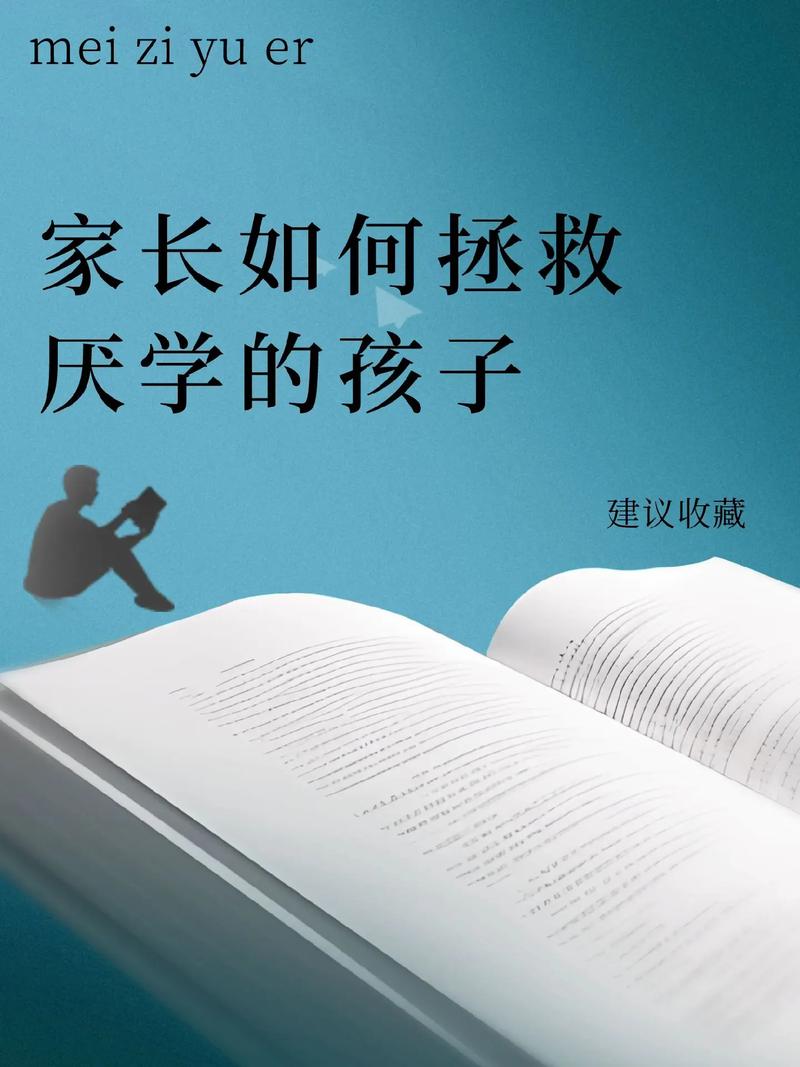(以下为正文部分,共计1987字)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星空中,沈雁冰(1896-1981)以"茅盾"为笔名,如同一颗璀璨的恒星,其光芒穿透时代阴霾,照亮了现代文学的发展之路,这位集文学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多重身份于一身的文化巨擘,用六十五载笔耕岁月,在文学创作与教育实践中构建起独特的精神坐标系,当我们拨开历史的迷雾,重新审视这位文学大师的传奇人生,会发现其生命轨迹中蕴含着超越时空的教育智慧。
钱塘江畔的觉醒者(1896-1916) 在杭州湾的涛声中,1896年7月4日诞生的沈德鸿(茅盾本名),自幼浸泡在书香世家的人文滋养里,其父沈永锡作为晚清秀才,突破传统教育桎梏,将《天演论》《瀛寰志略》等新学典籍引入家塾,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启蒙教育,在少年茅盾心中埋下变革的种子,湖州中学堂求学期间,他亲历辛亥革命浪潮,在《申报》上发表的时评《学生与社会》已显露出超越年龄的社会洞察力。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茅盾在严复、章太炎等大师云集的学术殿堂中,系统接触西方哲学与文学理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自修室研读《共产党宣言》英文原版时留下的批注,成为后来研究其思想转变的重要物证,这段求学经历不仅锻造了其深厚的学术根基,更塑造了其"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品格。
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1916-1927) 1916年入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为茅盾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在主持《小说月报》革新期间,他创造性提出"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将刊物从鸳鸯蝴蝶派的消遣文学阵地,转变为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平台,这一时期编纂的《中国寓言初编》与《童话》丛书,展现其早期教育理念——用生动文本培养青少年的批判思维。
1921年参与创建文学研究会,茅盾与郑振铎等人共同推动"为人生的艺术"运动,其撰写的《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等理论文章,系统构建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体系,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主持的"学生国学丛书"编纂工程,开创了古籍今注与青年阅读结合的典范,至今仍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参考书目。
革命洪流中的思考者(1927-1937)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茅盾隐居上海创作《蚀》三部曲,以文学解剖时代阵痛,这段蛰伏期诞生的《虹》《路》《三人行》等作品,突破传统教育小说范式,通过知识青年的人生抉择折射社会变革,1930年加入"左联"后,他主持的《文学》月刊成为培养青年作家的摇篮,张天翼、沙汀等文学新星在此崭露头角。
1933年问世的《子夜》,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育史诗,吴荪甫的实业救国梦与民族资本困境,构成生动的经济学教案;交易所的投机狂潮与工人运动浪潮,演绎着鲜活的社会学图景,这部"新儒林外史"不仅奠定茅盾的文学地位,更开创了文学参与社会教育的全新范式,据上海开明书店统计,抗战前该书已重印27次,成为大中学生理解社会现实的必读书目。
抗战烽火中的文化脊梁(1937-1949) 全面抗战爆发后,茅盾辗转香港、新疆、延安等地,在流徙中坚持文化教育事业,1938年主编《文艺阵地》期间,他首创"战地通讯"专栏,培养出碧野、于逢等战地作家,在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任教时,他设计的"比较文学"课程大纲,将维吾尔民间文学与汉族古典文学并置研究,这种跨文化教育理念在当时极具前瞻性。
1941年创作的《白杨礼赞》,作为现代散文经典入选两岸语文教材逾半世纪,文中"伟丈夫"的意象塑造,既是对民族精神的礼赞,也暗含人格教育的深意,1945年发表的《清明前后》,通过戏剧形式探讨战时经济问题,在重庆公演时引发知识界关于"文学的社会教育功能"的持续讨论。
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掌灯人(1949-1981) 担任首任文化部长期间,茅盾推动建立作家等级制度与稿酬体系,为职业作家培养奠定制度基础,他主持的"文学讲习所"(今鲁迅文学院前身),采用"创作实践+理论研讨"的培养模式,培育出邓友梅、玛拉沁夫等共和国第一代作家,1953年在全国文代会上提出的"文学应该帮助人民认识生活"主张,至今仍是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准则。
即使在特殊历史时期,茅盾仍以独特方式延续文化命脉,1978年将25万元稿费捐赠作长篇小说奖基金,这个以他名字命名的文学奖项,四十余年来激励着无数文学新人,晚年撰写的《回忆录》不仅具有史料价值,更展现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操守,其中关于"文学与教育互为表里"的论述,为当代人文教育提供重要启示。
教育理念的当代回响 茅盾的教育实践始终贯穿着"知行合一"的主线,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强调"不说教而寓教于乐",在作家培养中注重"生活体验优先于技巧训练",在文化普及中主张"雅俗共赏而非曲高和寡",其1934年发表的《儿童文学"》专论,提出的"培养鉴赏力比传授知识更重要"观点,与当下核心素养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在数字时代的今天,重读茅盾1942年在桂林师范学院的演讲记录颇具启示:"真正的教育不是往口袋里装石头,而是点燃心中的火把。"这种强调主体觉醒的教育哲学,与其文学创作中的人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他晚年主持修订的《红楼梦》中学生读本,通过分级注释与专题研讨的设计,至今仍是名著教育的典范。
站在新世纪的门槛回望,茅盾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文学遗产,更是一部鲜活的教育启示录,从钱塘江畔的私塾学童到文化部长,从小说月报改革到茅盾文学奖设立,他始终以文学为舟楫,摆渡着民族的精神启蒙,当我们在语文课本中与《白杨礼赞》相遇,在文学史课堂上讨论《子夜》的现代性,实际上都在参与这场跨越时空的教育对话,这位文化巨匠的人生轨迹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应当培养既能直面现实困境,又能仰望精神星空的完整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