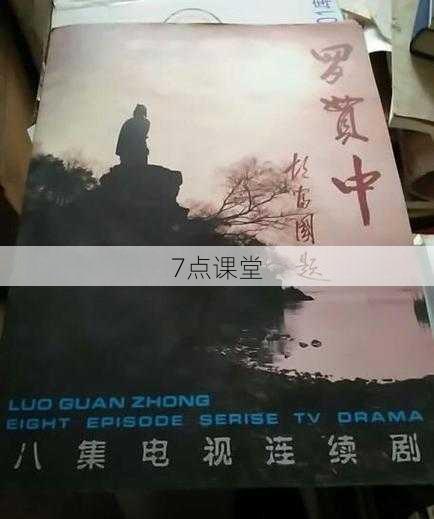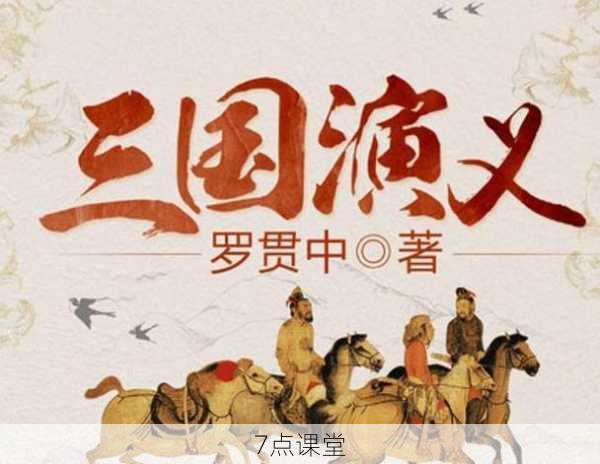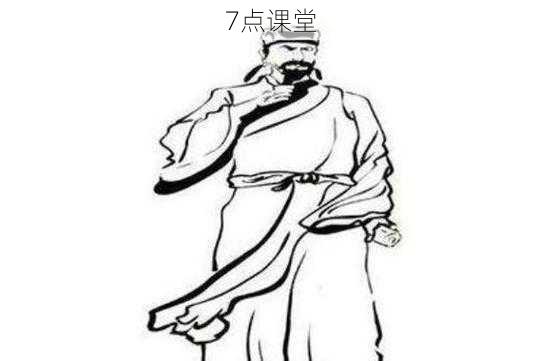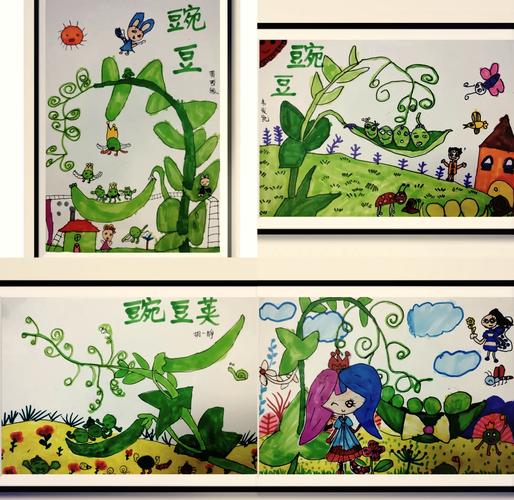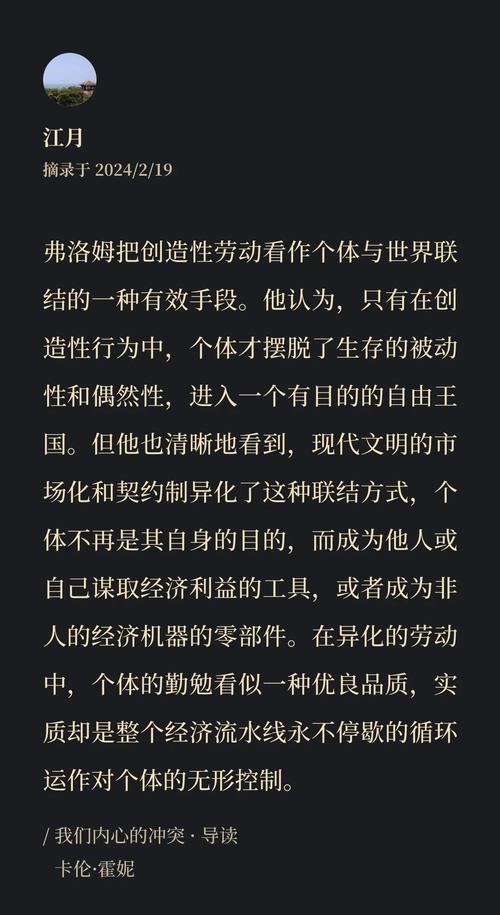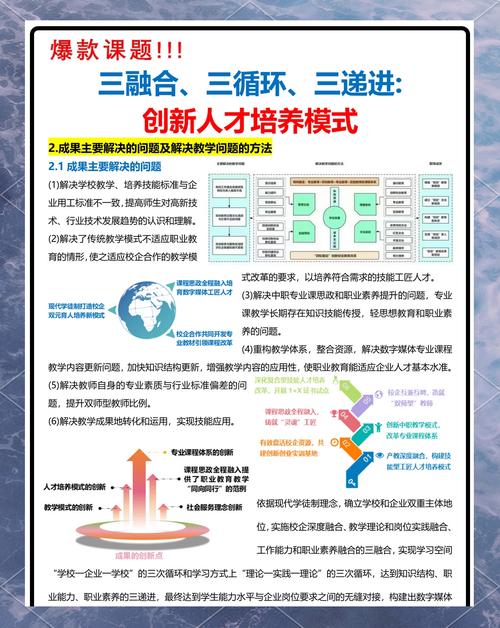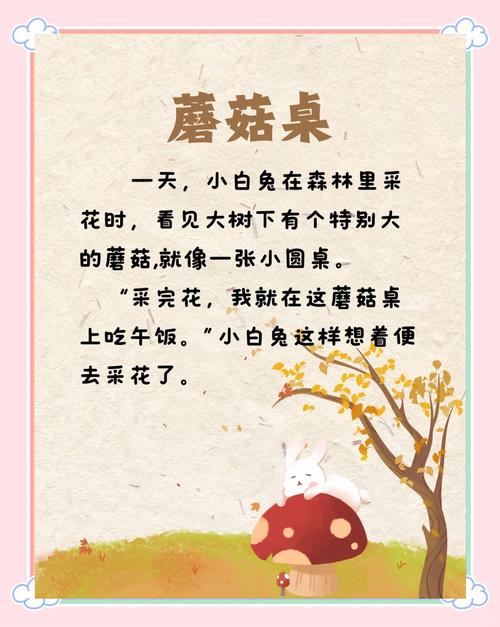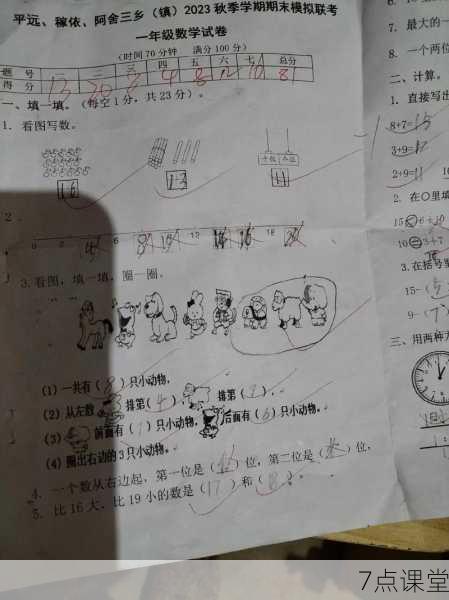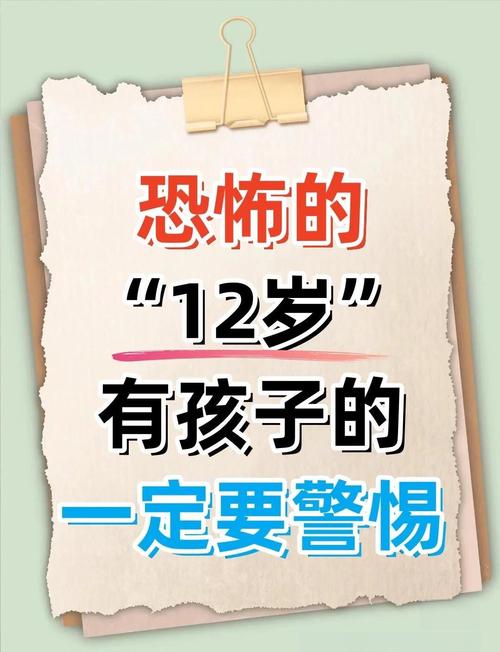在历史迷雾中寻找真实的罗贯中
关于罗贯中的生平,史书记载如同散落于古籍中的星辰,虽光芒璀璨却难以连缀成完整的图谱,元至治二年(1322年)至明建文三年(1401年)的时空坐标,框定着这位文学巨匠的生命轨迹,在杭州西子湖畔的瓦舍勾栏间,在山西清徐的乡野田畴上,历史学家们至今仍在为他的确切籍贯争论不休,这种身份之谜恰恰构成了理解其人其作的关键切口——当我们将罗贯中置于元明鼎革的特殊历史节点,方能真正理解《三国演义》中那挥之不去的兴亡之叹。
元末乱世中的文人抉择
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军起义的烽火燃遍中原,此时正值而立之年的罗贯中面临着知识分子的典型困境,元大都的科举考场早已荒废,江南文人群体在张士诚、朱元璋等割据势力间辗转求生,贾仲明《录鬼簿续编》中"遭时多故"的记载,暗示着罗贯中可能亲身参与过反元斗争,这种特殊经历在其作品中投射为对战争场面的精微描写:从官渡之战的粮草算计到赤壁火攻的战术推演,处处可见军事战略家的眼光。
《三国演义》的创作密码
建文年间付梓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实则是部历经三个世纪的集体创作,从宋元话本到元代杂剧,三国故事在民间已形成完整的叙事体系,罗贯中的创造性在于将市井文学提升为历史寓言——他刻意模糊了"拥刘反曹"的道德立场,转而以宿命论的笔调书写英雄末路,关羽败走麦城时的星陨异象,诸葛亮五丈原的将星坠落,这些充满谶纬色彩的描写,实则是元末战乱中百姓集体创伤的艺术转化。
跨时空的文学对话
比较视野下的研究更能彰显罗贯中的创作特质,与施耐庵《水浒传》的江湖叙事不同,罗贯中始终保持着史家的克制,他巧妙运用"七实三虚"的创作原则,在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注之间寻找平衡点,对曹操形象的塑造尤见功力:既保留其"治世能臣"的政治智慧,又通过"梦中杀人"等细节暗示权力异化,这种复杂性格的刻画,显然受到元杂剧中曹操"白脸奸臣"形象的影响,却展现出更高层次的历史思辨。
知识考古中的多重身份
20世纪新材料的发现不断重塑着罗贯中的形象,1931年郑振铎发现的《三遂平妖传》孤本,揭示了他作为神魔小说开创者的另一面相;天一阁藏《录鬼簿》中"乐府隐语,极为清新"的记载,则指向其散曲家的身份,近年山西发现的《罗氏家谱》,虽真伪尚存争议,却为我们勾勒出太原罗氏五代书香的家学脉络,这些碎片最终拼合出的,是位游走于雅俗之间的跨界文人。
时代精神的艺术转译
《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苍茫意象,实为元明易代之际文人群体心理的绝佳隐喻,罗贯中在历史叙事中寄寓着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思考:刘备集团"复兴汉室"的政治口号,暗合着元末起义军"重开大宋之天"的斗争策略;诸葛亮"鞠躬尽瘁"的忠臣形象,则是士大夫阶层对理想政治人格的终极想象,这种历史与现实的互文关系,使小说超越了通俗文学的范畴,成为解读14世纪中国社会的重要文本。
经典生成的传播密码
从嘉靖元年(1522年)的官刻版到万历年间余象斗的双峰堂本,《三国演义》的版本流变本身就是部生动的出版史,书商们通过增删评点、插画绣像等手段持续重构文本意义:叶昼托名李贽的评点本强调历史宿命论,毛纶、毛宗岗父子则强化尊刘贬曹的正统观,这种历时性阐释恰恰证明,罗贯中的创作早已突破个人范畴,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遗产。
跨越六百年的文化回响
当21世纪的读者在"三国杀"卡牌游戏中推演赤壁之战时,罗贯中创造的文学世界仍在持续生长,从京剧中"长坂坡"的经典唱段,到日本横山光辉的漫画改编,《三国演义》已然成为东方叙事美学的原型库,这种跨媒介、跨文化的传播奇迹,根源于罗贯中对人性本质的深刻把握——他在群雄逐鹿的宏大叙事中,始终凝视着个体在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
站在当代回望,罗贯中不再只是某个朝代的注脚,而是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枢纽,他以元末明初的动荡时局为熔炉,将史传文学、民间说唱、戏曲艺术熔铸为全新的文学形态,这种创造性转化的能力,正是中华文明历经沧桑仍保持活力的关键密码,当我们追问"罗贯中是哪朝人"时,真正探寻的是中国文学如何在历史转折中实现自我更新,以及经典作品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