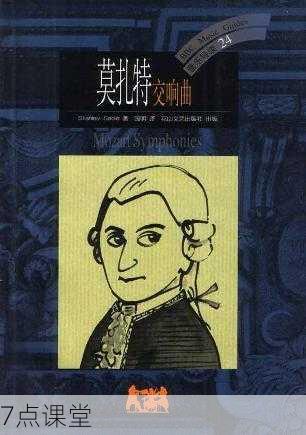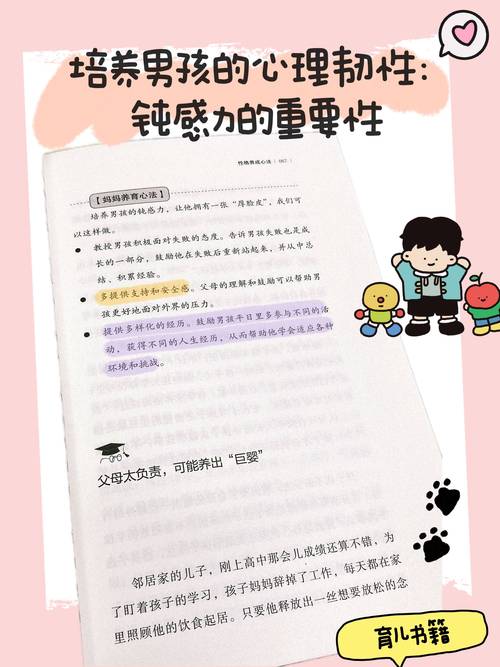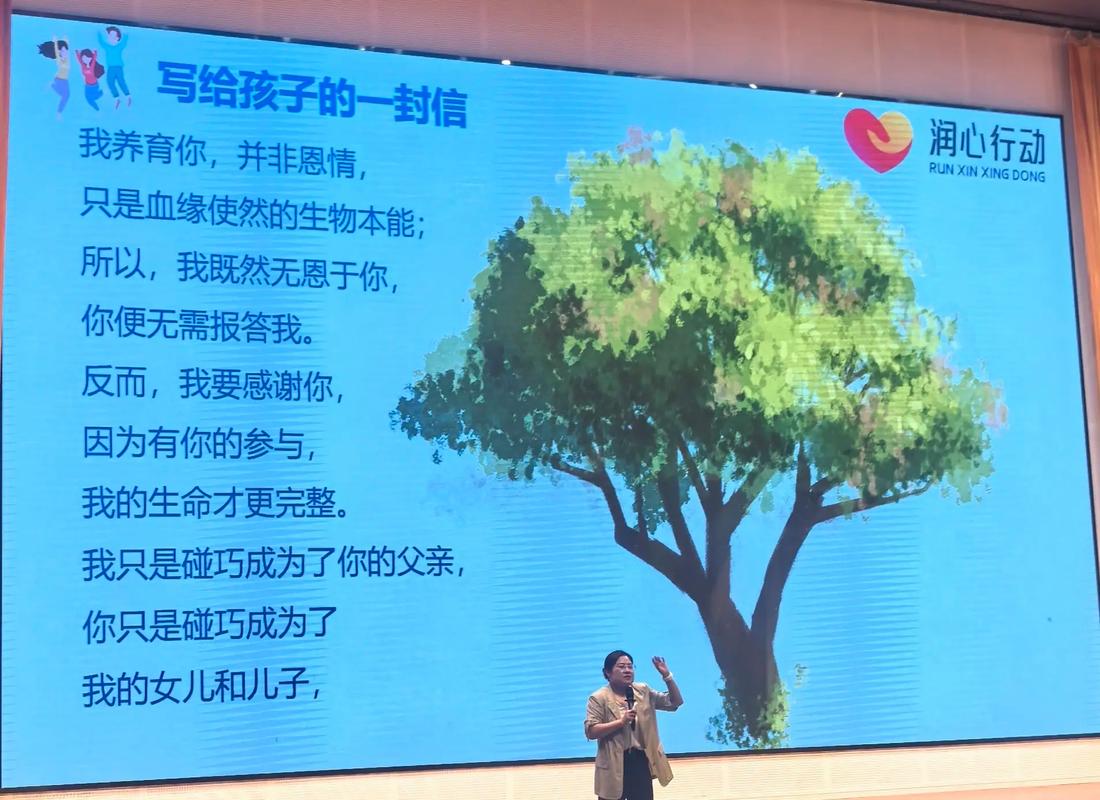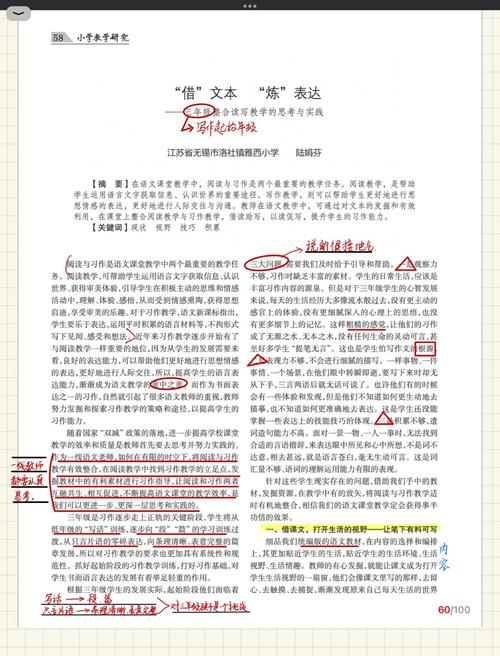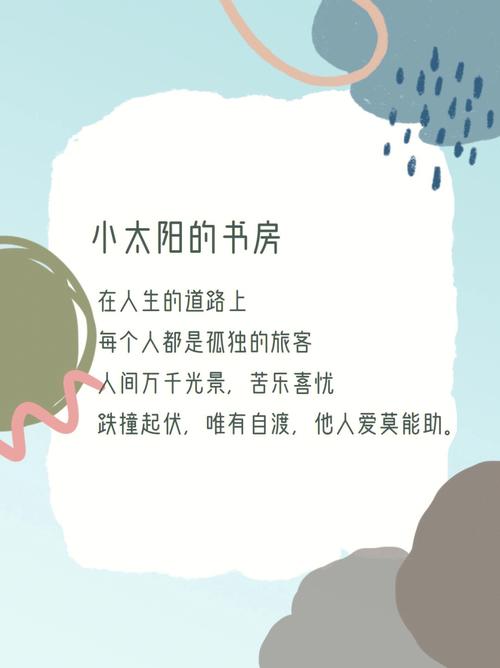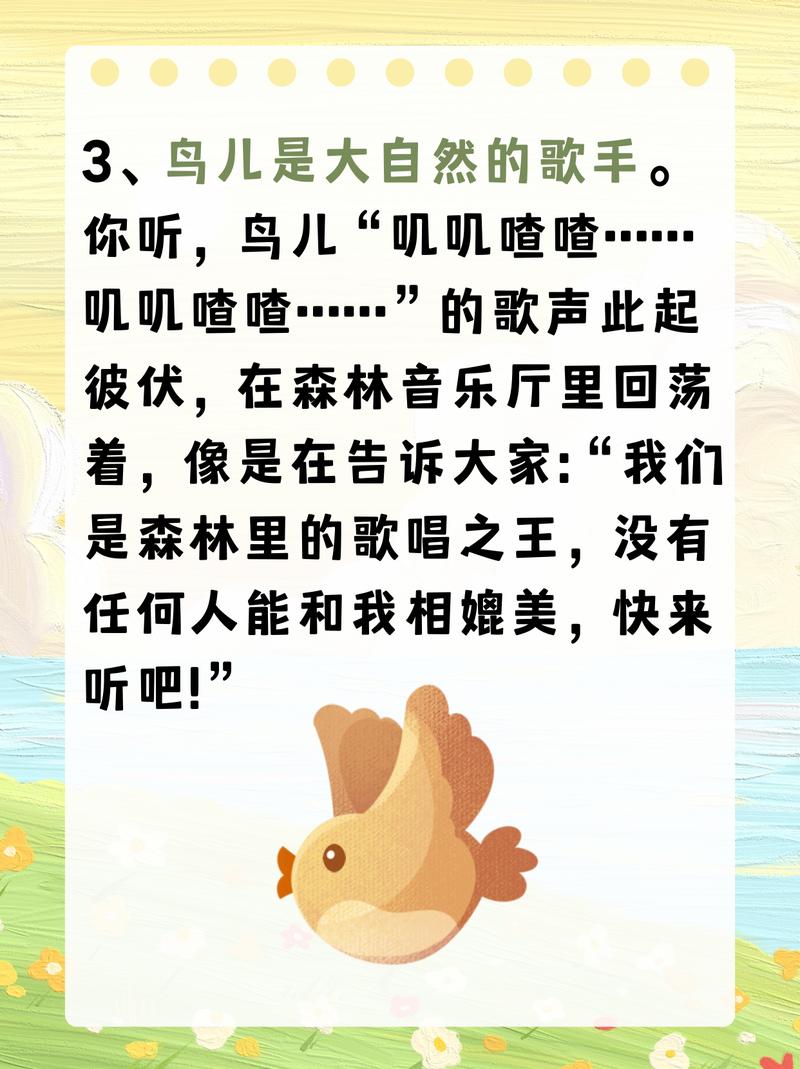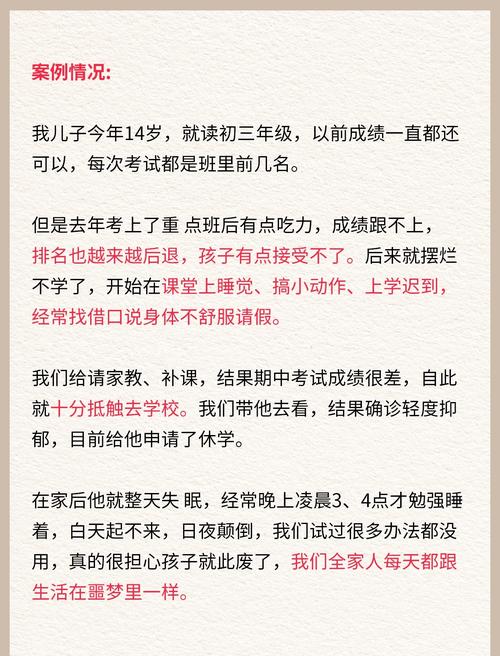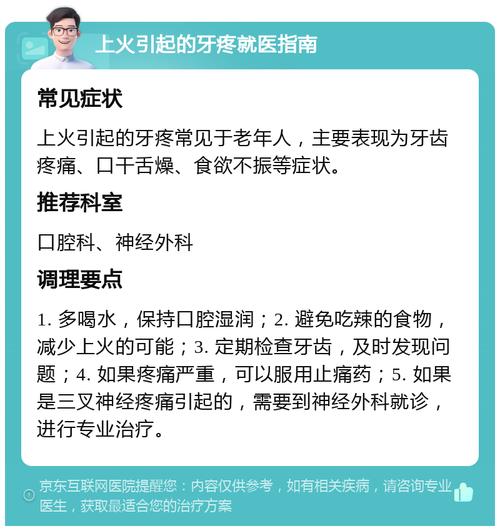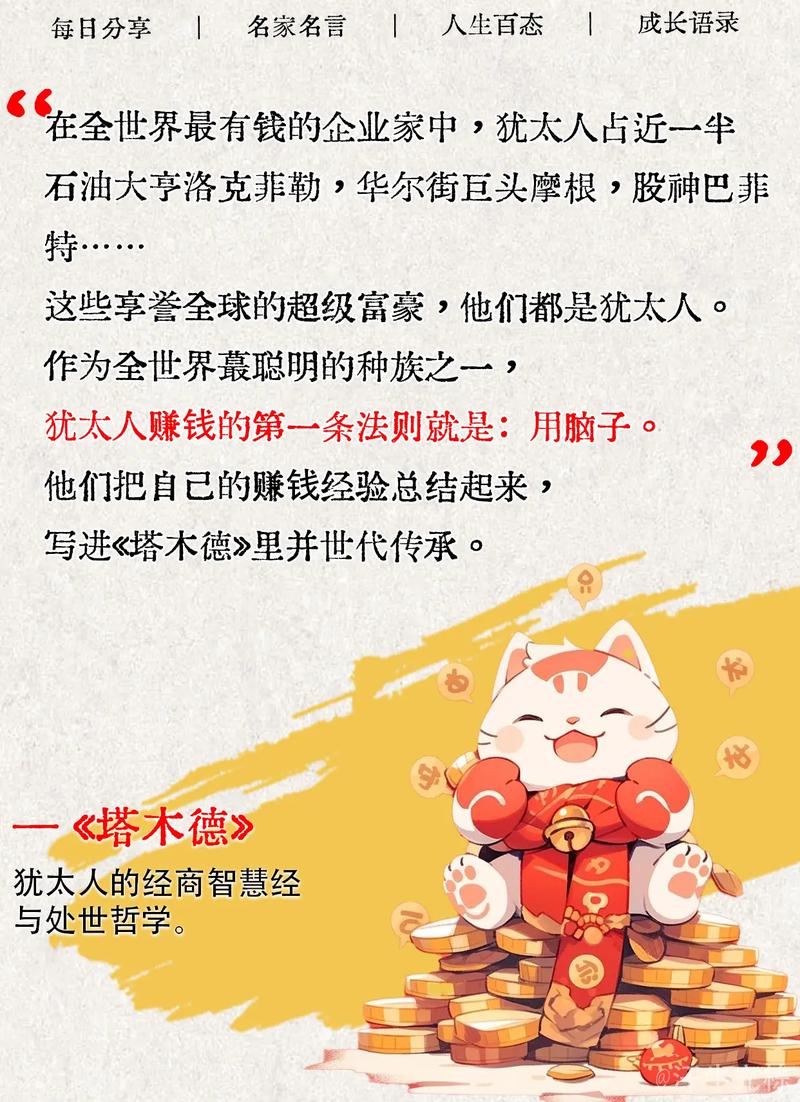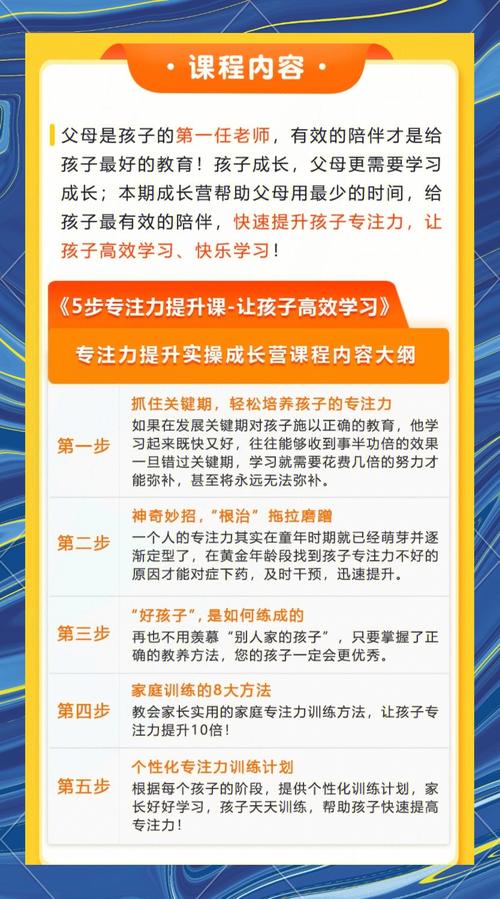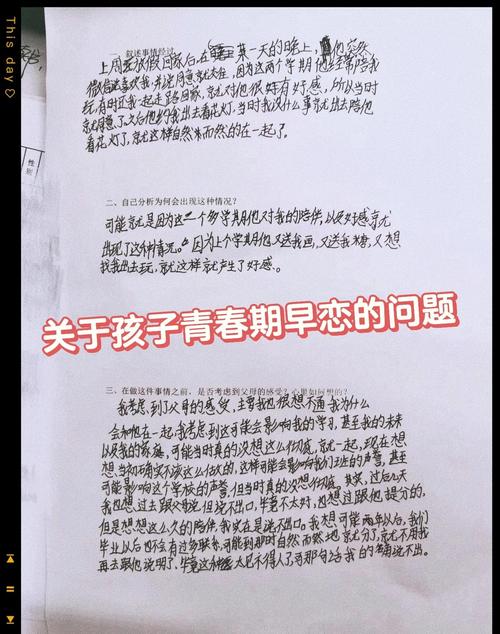当音乐厅的灯光渐暗,指挥棒划破寂静的瞬间,人类艺术史上最深邃的对话就此展开,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维也纳乐坛,两颗恒星以截然不同的轨迹划过天际——沃尔夫冈·阿玛迪乌斯·莫扎特与路德维希·凡·贝多芬,这场跨越时空的"天才对决",在当代音乐爱好者中引发的争论,恰似巴洛克时期复调音乐中相互追逐的声部,在对抗与融合中构建出永恒的艺术图景。
要理解这场比较的实质,需先还原历史语境,莫扎特(1756-1791)降生于萨尔茨堡宫廷乐师家庭,4岁作曲、6岁巡演的传奇经历,使他成为启蒙运动时期"天赋论"的最佳注脚,而贝多芬(1770-1827)诞生于波恩平民家庭,22岁才在维也纳确立地位的人生轨迹,则暗合了法国大革命后个人奋斗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背景的差异,在两人创作中投射出泾渭分明的美学追求:前者将古典主义的形式美推向极致,后者则为浪漫主义的自由精神开辟道路。
在音乐语言的建构层面,莫扎特的创作犹如精密的数学方程式,其《G大调弦乐小夜曲》(K.525)中,每个音符都严格遵循奏鸣曲式的对位法则,却在规整框架内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旋律流动性,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境界,在歌剧《费加罗的婚礼》中达到巅峰——复杂的多声部重唱既能严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又精准刻画出人物性格的微妙差异,相较而言,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彻底打破了交响乐的结构范式,将传统四乐章扩展为具有叙事性的宏大史诗,特别是在谐谑曲乐章中,突兀的节奏变化与动态对比,预示着浪漫主义音乐的革命性转向。
创作方法论的分野更值得玩味,莫扎特的手稿往往洁净如誊写本,传说中他在脑中完成作曲的"神迹",实则是长期严格训练的必然结果,其作品目录显示,仅1788年夏季就连续完成第39、40、41号三部交响曲,这种高效创作建立在对古典形式的绝对掌控之上,反观贝多芬的草稿本,布满修改痕迹的《槌子键琴奏鸣曲》手稿,揭示出"苦吟派"创作特征,他在耳聋加剧时期创作的《第九交响曲》,通过将席勒诗篇引入交响乐章,实现了音乐表现形式的根本性突破。
历史影响力的比较需采用长时段视角,莫扎特在短暂35年人生中创作600余部作品,其旋律天赋直接催生了后世"莫扎特效应"的心理学研究,但更具深意的是,他在《魔笛》中开创的德语歌剧传统,为瓦格纳的乐剧改革埋下伏笔,贝多芬则通过《庄严弥撒》等晚期作品,将音乐提升至哲学思辨的高度,其《第五交响曲》的四音符动机,不仅是音乐史上最著名的"命运敲门声",更成为人类对抗困境的精神图腾,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大师的影响存在有趣的时空错位:勃拉姆斯因畏惧贝多芬的交响乐遗产而迟迟不敢创作交响曲,而肖邦的钢琴创作却处处可见莫扎特式的精致语法。
从艺术教育维度审视,两位大师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学习范式,莫扎特案例证明,早期音乐浸染与系统训练能培育出惊人的形式敏感度,其《土耳其进行曲》至今仍是钢琴启蒙教育的经典教材,而贝多芬的成长轨迹则彰显出后天突破的可能性,其32首钢琴奏鸣曲构成的"新约圣经",完整记录了从古典范式到浪漫表达的蜕变过程,现代脑科学研究表明,莫扎特作品规律的周期性结构能有效激活大脑α波,而贝多芬音乐中的冲突性张力则显著提升皮质醇水平,这种生理反应的差异恰是二者美学特质的最佳印证。
在文化符号的构建层面,"莫扎特神话"与"贝多芬崇拜"折射出不同的时代精神,19世纪浪漫主义者将贝多芬塑造为"对抗命运的普罗米修斯",其蓬乱头发下的坚毅面容成为艺术家反叛精神的经典icon,而莫扎特则被简化为"神童"代名词,直到20世纪音乐学家通过分析其信件,才还原出那个在宫廷体制中挣扎求存的真实艺术家形象,这种符号化过程导致大众认知的偏差:莫扎特被视为优雅的化身,却忽视其《d小调钢琴协奏曲》(K.466)中的悲剧性张力;贝多芬被定格为革命者,但其《第六交响曲》展现的自然主义情怀常遭忽视。
当代音乐学者克雷格·莱特在《音乐如何运作》中指出,比较两位大师的本质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永恒对话,当古尔德用现代钢琴演绎莫扎特奏鸣曲时,刻意压制的浪漫处理反而凸显了作品的建筑美感;当伯恩斯坦指挥贝多芬时,夸张的力度对比恰是对乐圣精神的忠实诠释,这种诠释学的差异证明,两位大师共同构建了西方音乐的双螺旋结构:形式与内容、理性与激情、传统与创新的永恒辩证。
在流媒体时代,这场比较呈现出新维度,据统计,莫扎特作品的全球播放量是贝多芬的1.7倍,但贝多芬乐谱的改编版本数量远超前者,这揭示出当代受众的接受差异:莫扎特的旋律更契合碎片化聆听,而贝多芬作品的戏剧性需要深度沉浸,教育工作者应当引导学生超越简单比较,转而关注两者如何共同拓展了音乐的表现疆域——正如马勒所说:"交响乐必须包容整个世界",而这个世界既有莫扎特的澄明星空,也有贝多芬的暴风骤雨。
当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音乐厅穹顶之下,我们会发现这场跨越两个世纪的对话从未真正结束,或许正如勋伯格所言:"贝多芬打开的门,莫扎特早已在里面等候。"在人类追求艺术完美的永恒征程中,萨尔茨堡的神童与维也纳的斗士,终将在永恒的和声中达成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