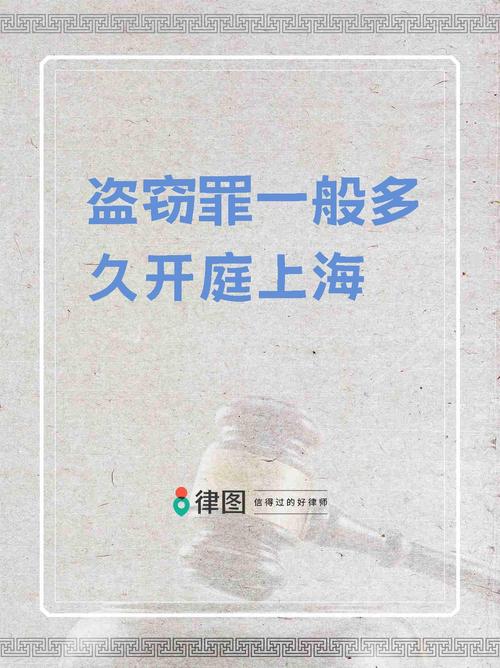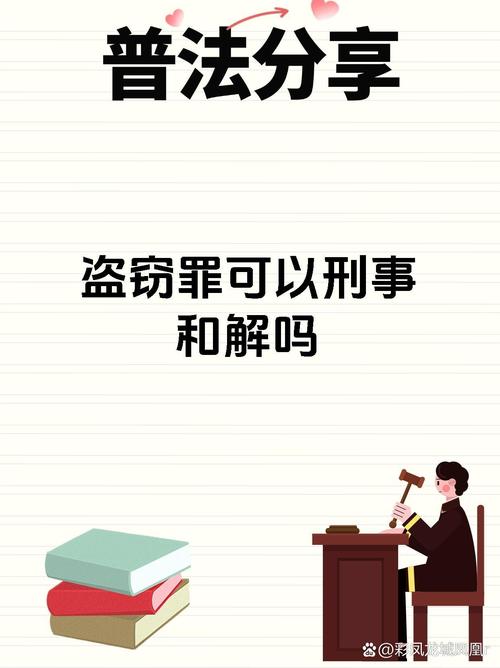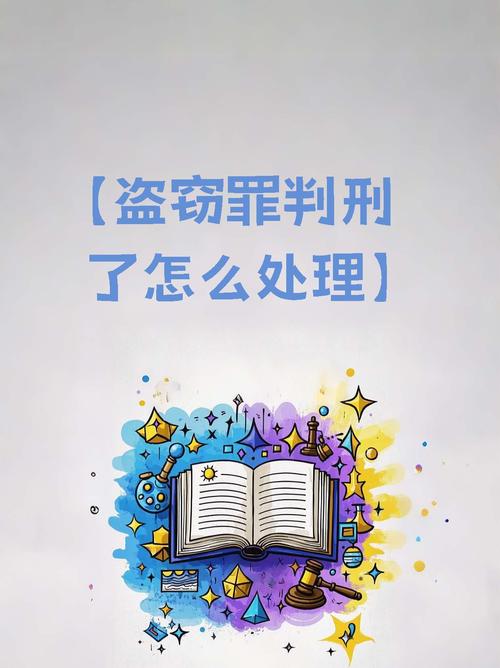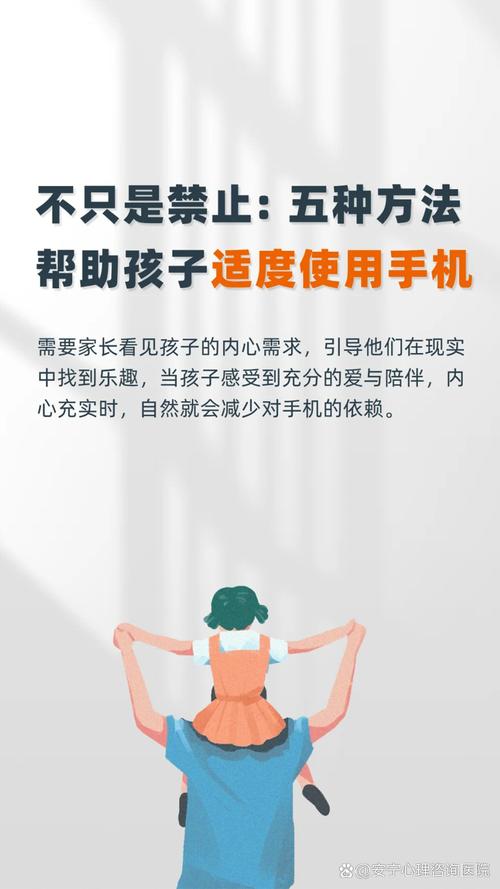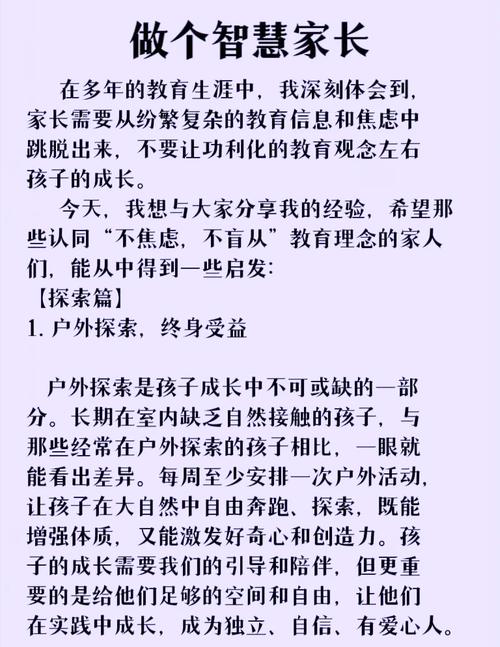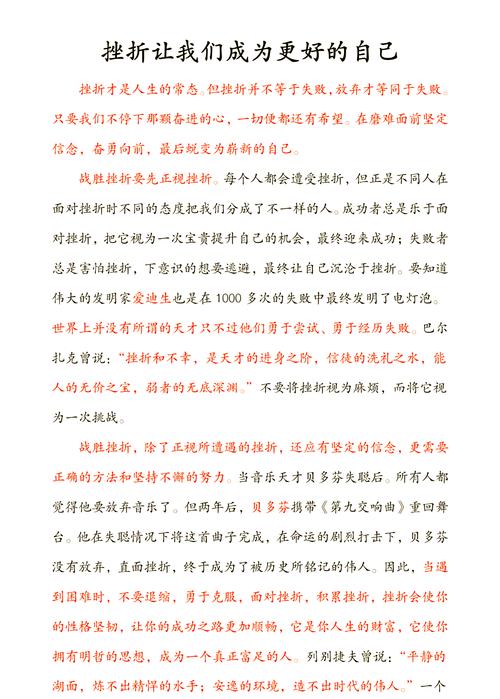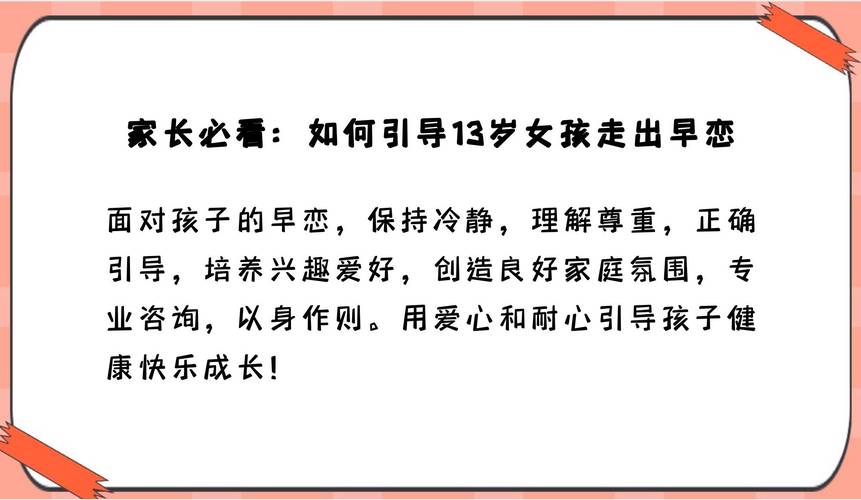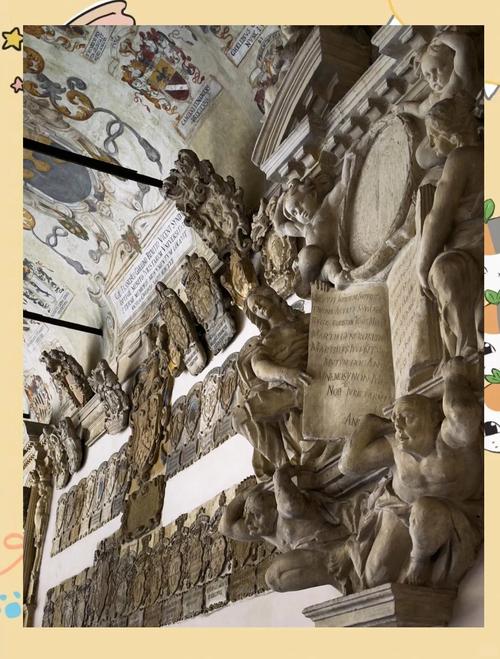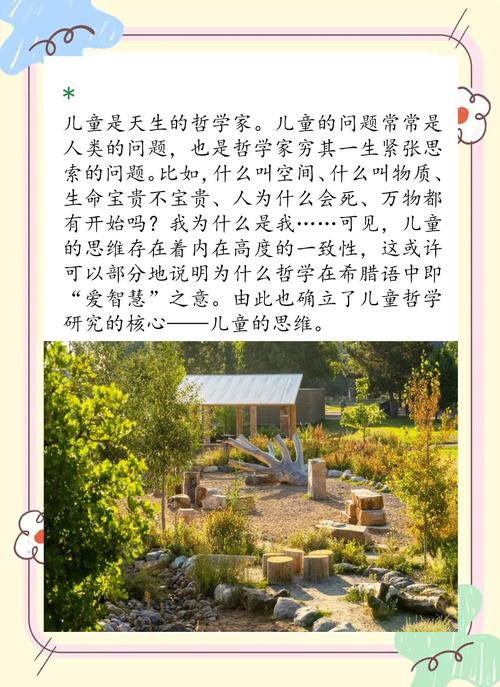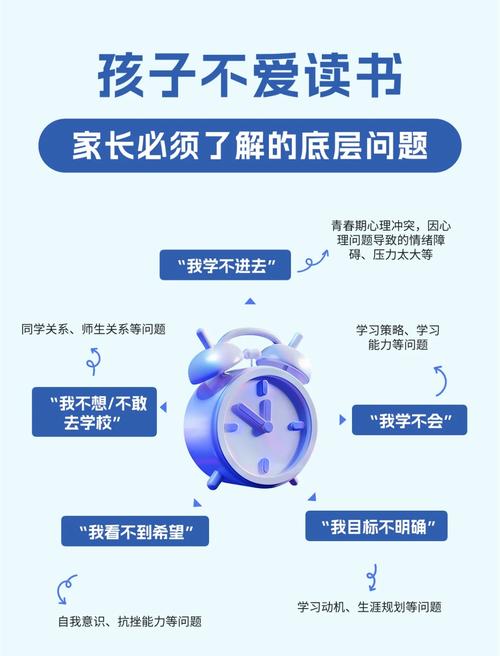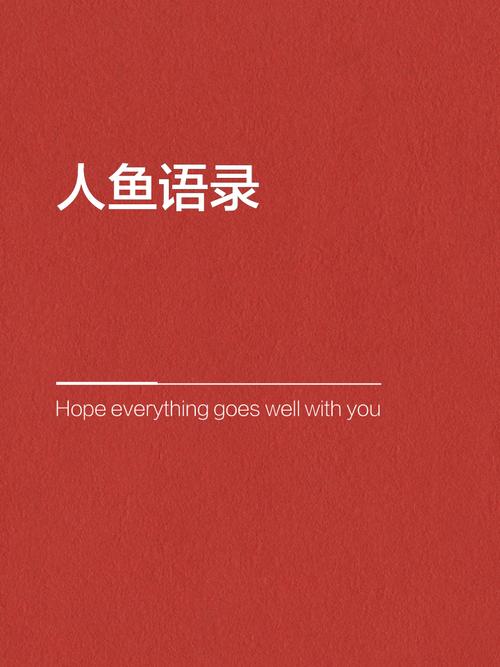在维多利亚时代儿童文学研究者玛格丽特·布伦登看来,《爱丽丝漫游奇境》第十一章"谁偷走了馅饼"堪称文学史上最富教育意义的荒诞场景,这个看似滑稽的法庭审判,实则以隐喻之笔揭开了19世纪教育体系中的深层痼疾,当我们穿越红心王后夸张的审判庭,会发现这场关于馅饼失窃的闹剧,恰似一面照妖镜,映照出传统教育中权威崇拜、逻辑缺失与真相扭曲的三重困境。
审判庭里的教育剧场 红心王后头戴三重王冠端坐审判席的场景,令人联想到维多利亚时代教室里的典型画面:教师端坐讲台,学生垂首聆听,在"馅饼失窃案"的审理过程中,法官与陪审团的角色错位、证据规则的混乱,恰似当时教育体系中知识传授的失序状态,爱丽丝作为旁观者提出的质疑——"这根本不算审判",正暗合教育改革者对填鸭式教学的批判。
历史档案显示,1870年英国颁布的《基础教育法》虽普及了义务教育,却将课堂异化为知识审判庭,教师如同红心王后挥舞着"砍头"的教鞭,学生则像扑克牌卫兵机械复述着"馅饼属于王后"的既定结论,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的,恰似法庭上那些盲目抄写"重要废话"的陪审员——娴熟于记录形式,却丧失思考本质。
馅饼隐喻下的认知暴力 在文本细读中,"馅饼"的象征意义值得深究,这道本应共享的知识盛宴,却被异化为权力斗争的工具,红心杰克被指控盗窃的罪名,恰似传统教育中对学生好奇心的定罪,当爱丽丝指出"你们连馅饼是什么都没说明"时,她触碰的正是教育现场最尖锐的痛点——脱离现实的知识传授。
教育史学家彼得·坎宁安的研究表明,19世纪课本中30%的内容属于与现实脱节的教条,就像审判庭里无人追问馅饼的原料与归属,课堂上也鲜少探讨知识的本源,这种教育暴力在文本中具象化为红心王后的经典台词:"先判决,后审判",暴露出以结论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对思维过程的践踏。
扑克牌卫兵与标准化教育 十二位陪审员机械书写的场景,堪称工业革命时期教育流水线的绝妙隐喻,他们用石笔在石板上的刻写,与当时盛行的石板教学法形成互文,这些失去面孔的扑克牌人偶,正是标准化教育产物的生动写照——整齐划一却丧失个性,勤勉记录却拒绝思考。
比较教育学家安迪·格林指出,这种培养"人形石板"的教育模式,导致19世纪英国学生的创造力评估值较德国同龄人低42%,就像最终被塞进钱袋的陪审团,标准化教育将鲜活的思维装入统一的认知模具,当爱丽丝将蜥蜴比尔倒着写出庭时,这个细节暗示着突破规范的可能,却立即遭到体制的压制。
柴郡猫的微笑:批判性思维的觉醒 在这场荒诞审判中,柴郡猫若隐若现的微笑构成重要教育意象,它出现在爱丽丝认知动摇的时刻,恰似批判性思维的灵光闪现,当整个法庭陷入"砍头"威胁制造的恐惧时,唯有漂浮的微笑保持着超然的审视姿态,这暗示着独立思考精神对威权教育的消解。
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证实,类似柴郡猫的"第三视角"能提升73%的元认知能力,爱丽丝从最初被动旁听到最终推翻陪审席的成长轨迹,印证了杜威"做中学"理论的实效性,当她说出"你们不过是一副纸牌"时,完成了对教育权威的解构,这种觉醒比任何课堂说教都更具教育价值。
重构教育现场的"馅饼配方" 穿越文学隐喻回归教育现场,我们需要重新烘焙知识的"馅饼",首先应以"馅饼失窃案"的悬疑性激发探究热情,而非直接宣判标准答案,其次要建立民主化的"审判"程序,让师生共同参与知识建构,最重要的是保留柴郡猫式的思维空隙,在确定性与开放性间保持张力。
芬兰教育改革的成功案例为此提供注脚:其课堂讨论《爱丽丝》时,教师会引导学生设计"馅饼案"的替代性审判,这种教学法使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提升28%,道德判断力提高35%,正如卡罗尔通过荒诞揭示真理,当代教育者更需要用创新思维烹制知识盛宴。
当红心王后的法庭在爱丽丝的觉醒中崩塌,这个经典场景为教育者敲响警钟:任何将知识异化为权力道具的教育,终将在新时代的冲击下分崩离析,重读"馅饼失窃案",我们当警惕教育现场中的"扑克牌卫兵",更要培养能看穿"纸牌屋"的清醒目光,因为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复现既定的审判,而在于培育敢于质疑"谁偷走了馅饼"的探索精神——这或许就是卡罗尔留给后世最深刻的教育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