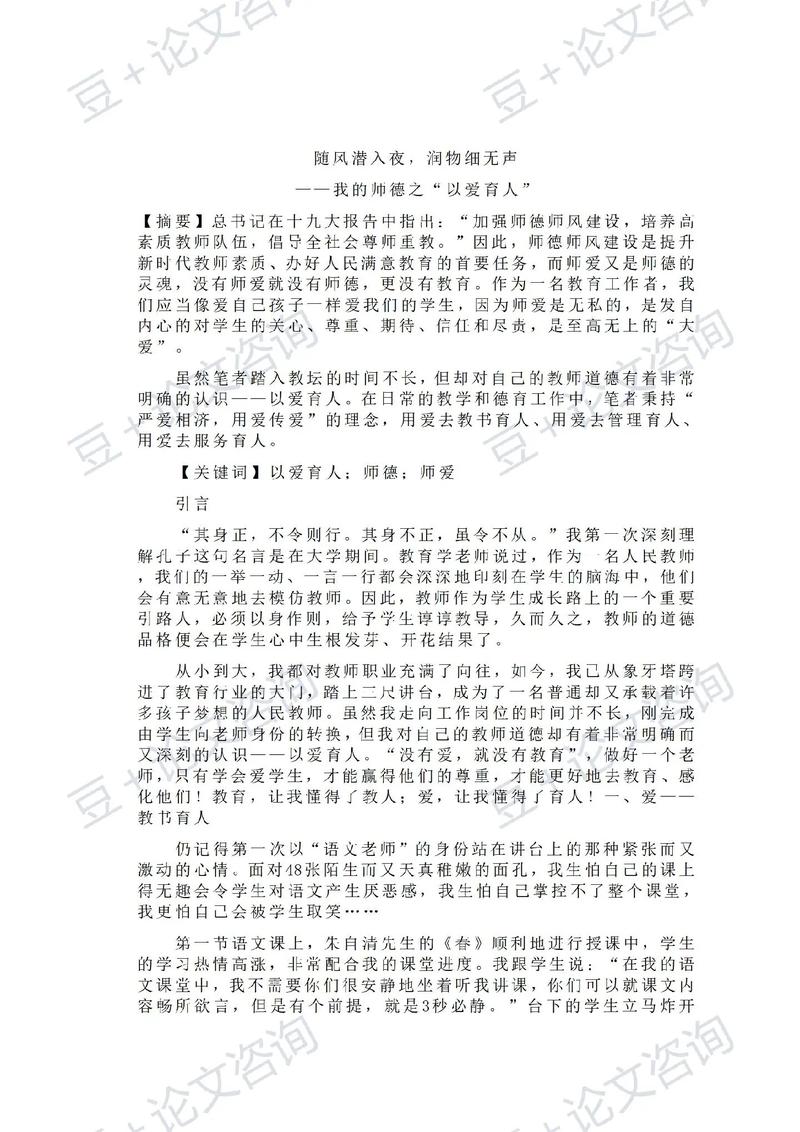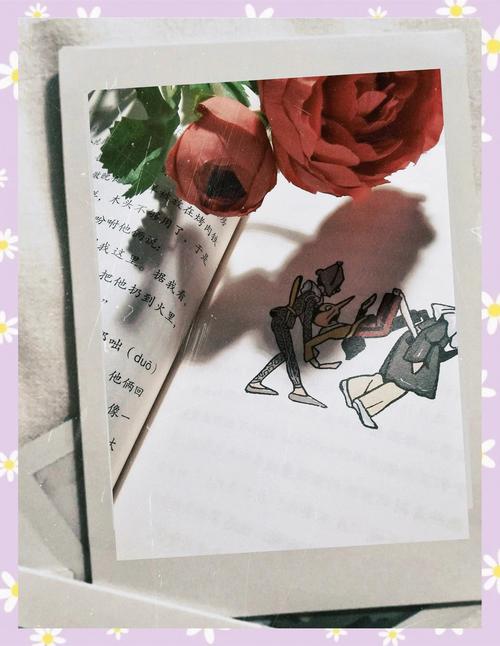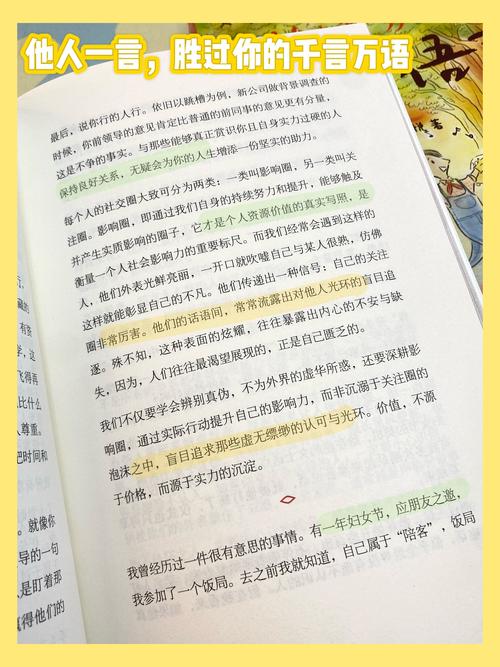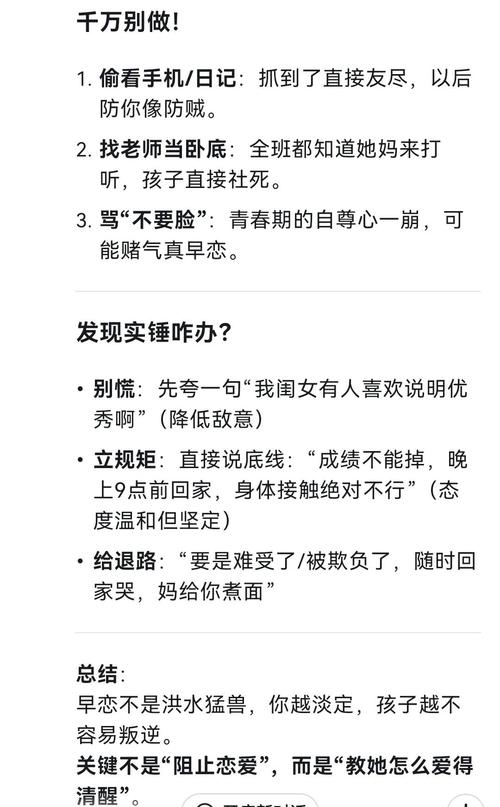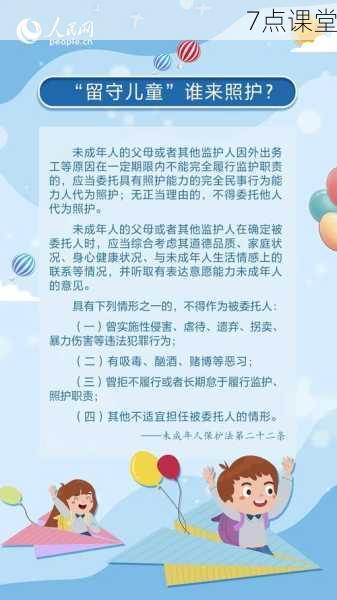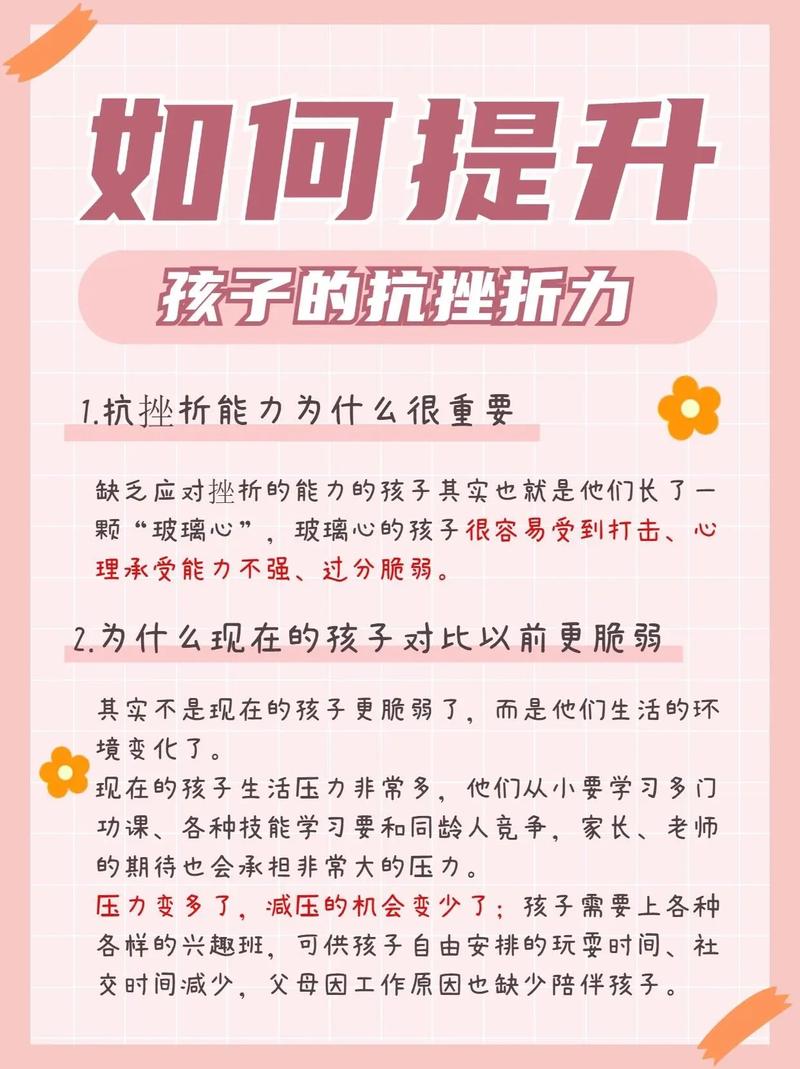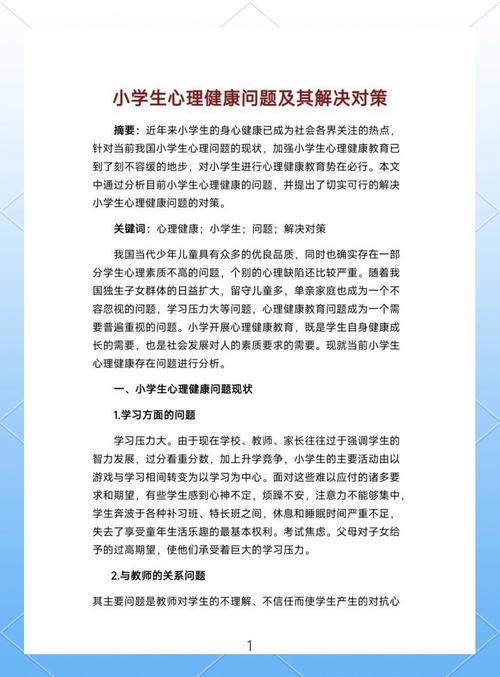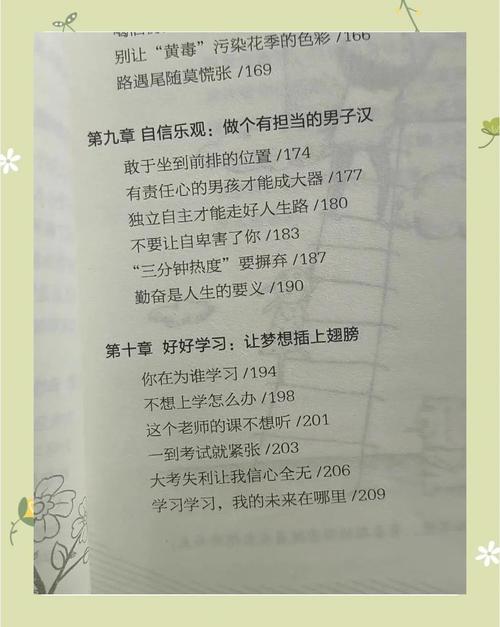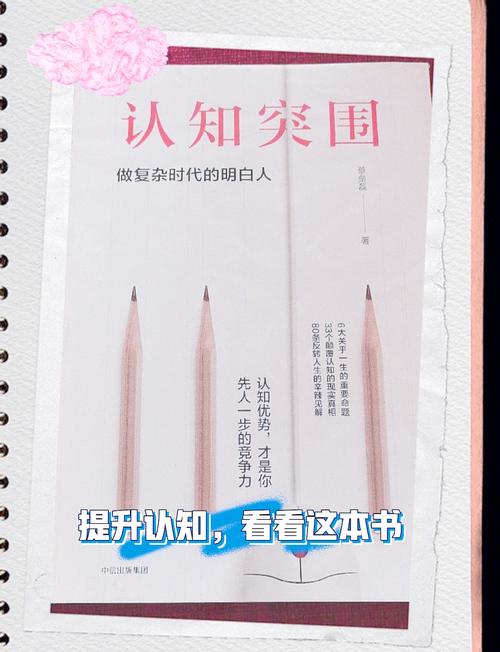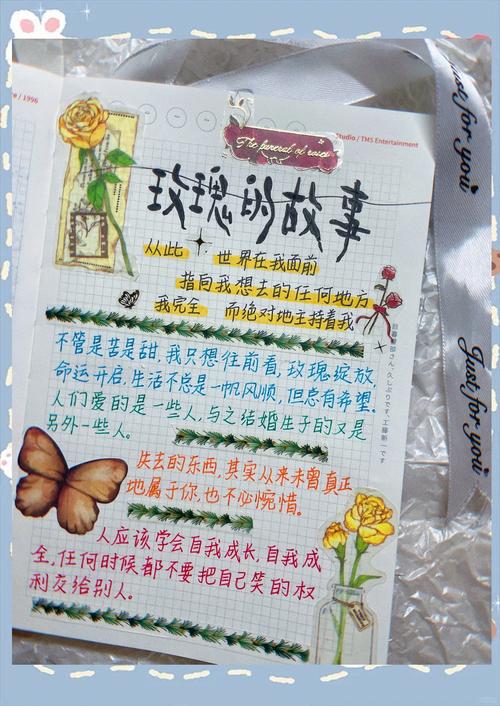当科洛迪的鹅毛笔在稿纸上写下《木偶奇遇记》第三十三章的最后一个句号时,这个诞生于1883年的寓言故事终于完成了它最核心的叙事闭环——木偶匹诺曹在经历了被鲨鱼吞噬、拯救父亲、自我牺牲等考验后,最终获得了人类的血肉之躯,这个看似简单的童话结局,实则蕴含着深刻的教育哲学,在当代教育语境下重新审视这个经典章节,我们会发现其中折射出的成长密码远比表面呈现的更为复杂精妙。
谎言叙事中的成长悖论 在第三十三章的核心情节中,匹诺曹向蓝发仙女坦白自己曾在学校偷懒的情节,这个看似普通的认错场景实则构成了全书的叙事枢纽,当木偶的鼻子不再因为谎言而变长,这个超现实设定消失的时刻,恰恰标志着其人性的真正觉醒,这种叙事安排揭示了一个重要的教育真相:道德内化必须经历从外部规训到内在自觉的转化过程。
匹诺曹的木质身体象征人类与生俱来的原始本能,而不断生长的鼻子则代表着社会规范对个体的约束,当这种外在约束机制最终消失时,说明道德准则已经完成了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化,现代教育心理学研究证实,儿童道德发展确实遵循着类似的轨迹: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指出,7-12岁的儿童正处于从他律道德向自律道德过渡的关键期,这与匹诺曹的成长轨迹高度吻合。
家庭教育中的镜像投射 杰佩托在鲸腹中的困境,构成了第三十三章最具隐喻性的场景,这位执着于雕刻人偶的老木匠,最终却被困在自己创造物的象征空间里,这个设定本身即是对教育者角色的深刻反思,当匹诺曹划着小船穿越黑暗的海洋实施救援时,传统的教育权力结构发生了戏剧性倒置。
这种角色转换揭示了家庭教育的本质特征:真正的教育永远是个双向建构的过程,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在这里得到完美印证——教育者创设的"认知支架"必须与学习者的实际发展水平保持动态平衡,杰佩托的被困状态暗示着传统权威式教育的局限性,而匹诺曹的救援行动则象征着新生代突破既定框架的可能性,这种代际互动中的张力,恰恰是推动教育发展的核心动力。
苦难教育的双面性解读 从被鲨鱼吞噬到冒险救援,第三十三章中密集的苦难叙事常常被简单解读为"善有善报"的道德训诫,但若深入分析匹诺曹在海底的蜕变过程,会发现其中包含着更为复杂的教育隐喻,木偶在黑暗中保持的微光,既是物理层面的磷火,更是人性觉醒的精神之光。
现代创伤理论认为,适度的挫折体验对人格发展具有建构性作用,匹诺曹在鲸腹中经历的孤立无援,实则创造了必要的"发展停滞期",这种脱离常规环境的状态迫使他调动内在潜能,但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叙事也暗含着将苦难浪漫化的危险倾向,正如卢梭在《爱弥儿》中强调的:自然教育需要控制痛苦的剂量,过度创伤反而会造成人格扭曲。
仪式化成长的社会学意义 蓝发仙女赐予匹诺曹人类身份的仪式场景,构成了全书最具象征意义的时刻,这个转化仪式包含着三重教育隐喻:身体性的(木偶变为人)、社会性的(获得合法身份)、精神性的(道德觉醒),人类学研究表明,成年礼等通过仪式对个体社会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当代教育场域中,这种仪式化过程被具象化为各种毕业典礼、成人仪式,但《木偶奇遇记》提醒我们,真正的成长仪式不应停留于形式,而应像匹诺曹的转变那样,是内外变革的同步完成,当教育机构越来越依赖标准化测试来认证成长时,这个童话反而凸显了质性评价的重要性。
教育乌托邦的现实映射 第三十三章创造的完美结局——坏孩子变成好学生,破碎家庭重获团圆——本质上是一个精心构筑的教育乌托邦,这种叙事满足着人们对理想教育的永恒期待,但也遮蔽了现实教育过程的复杂性和反复性,将这种乌托邦叙事置于19世纪末的意大利社会背景中考察,会发现其暗含着对工业化时代教育异化的批判。
科洛迪生活的年代正值欧洲义务教育制度确立期,标准化工厂式的教育模式开始普及,匹诺曹从拒绝上学到主动求学的转变,既是对读写能力重要性的肯定,也隐含着对机械教育的反思,这种双重性在当代更具启示意义: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更需要思考教育的本质究竟是规训还是解放。
重读《木偶奇遇记》第三十三章,我们得以跳出儿童文学的简单框架,在更深层面审视教育的本质,匹诺曹的鼻子停止生长之时,恰是教育最应该开始的时刻——当外在约束消失后,如何维持内心的道德准则?当权威庇护退场后,如何建立自主成长能力?这些叩问穿越三个世纪依然振聋发聩,在技术理性主导的当代教育中,这个木偶变人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永远是关乎心灵的技艺,是帮助每个个体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类之光"的漫长旅程。
(全文共1598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