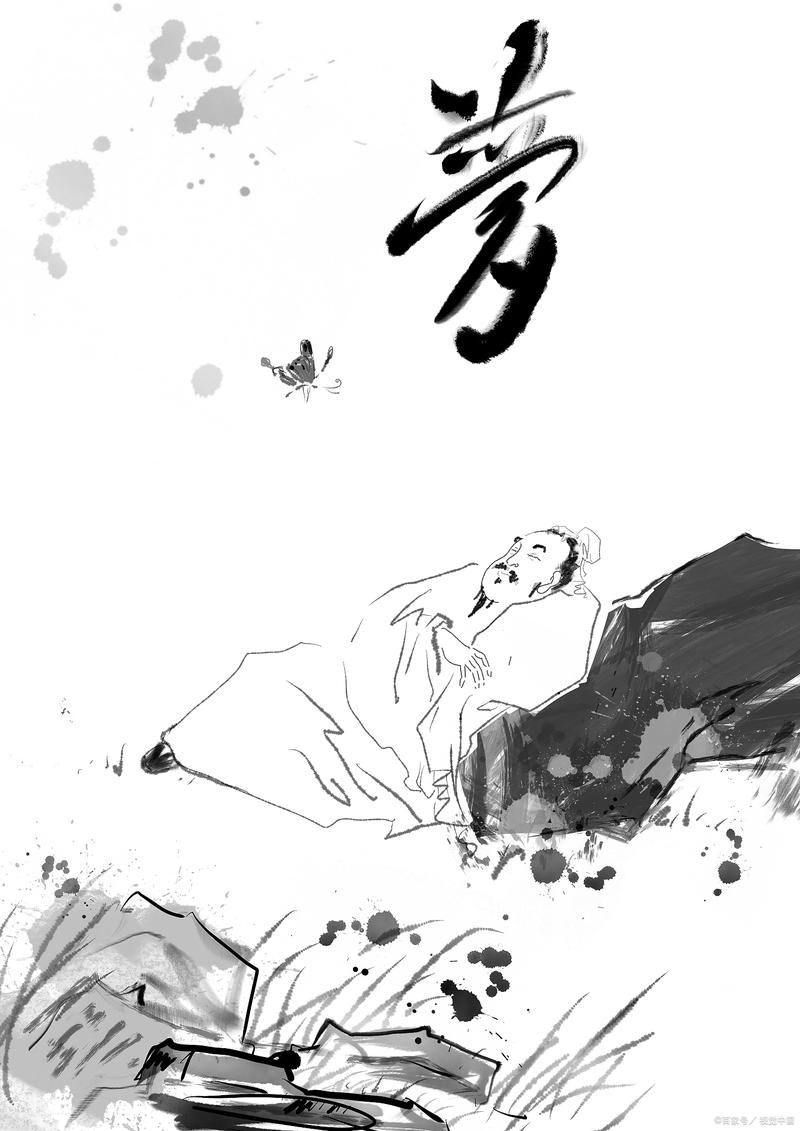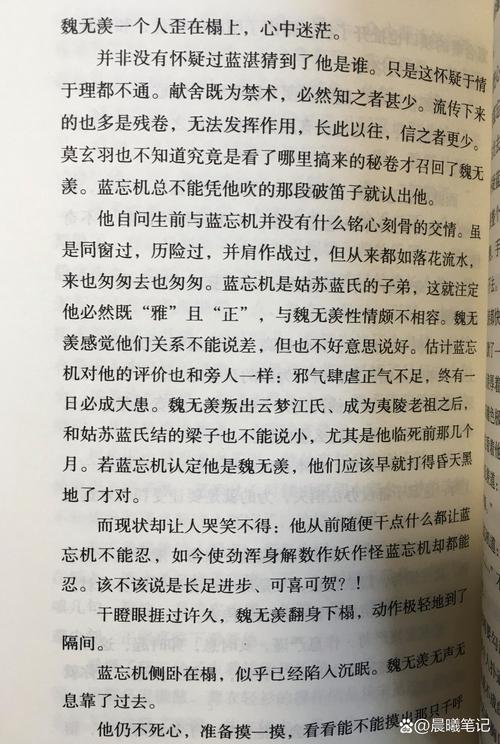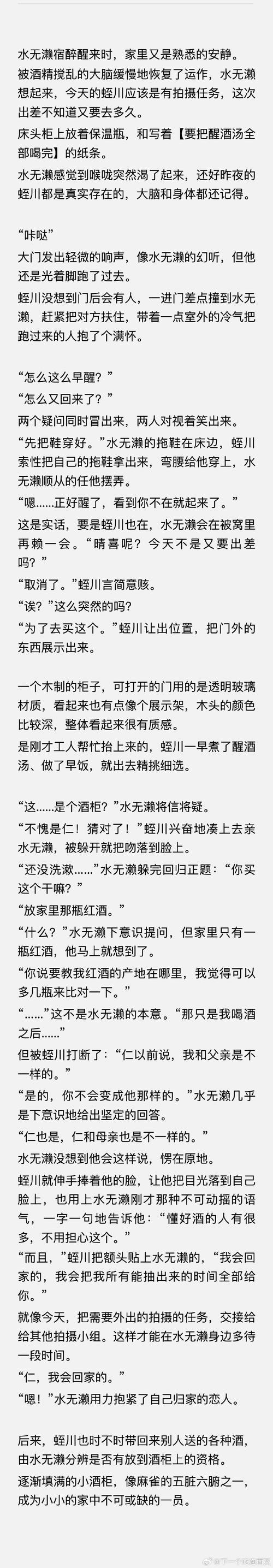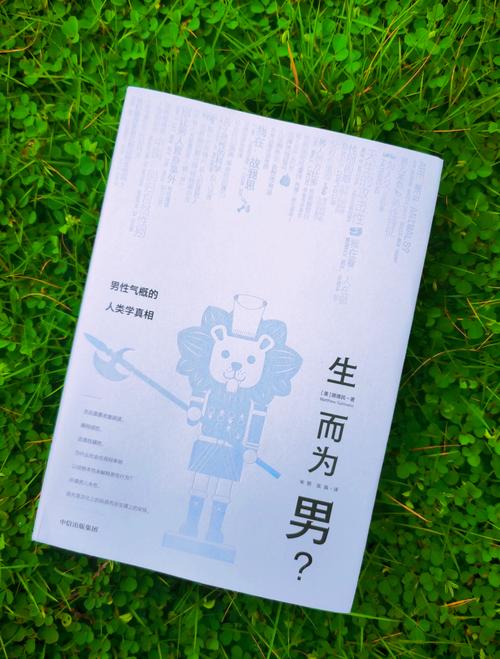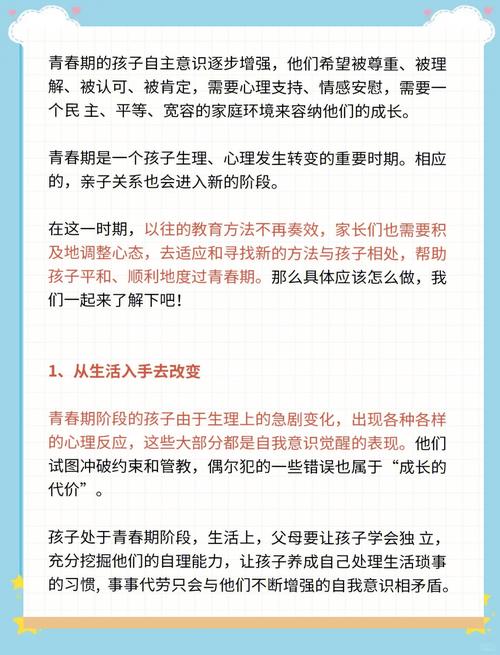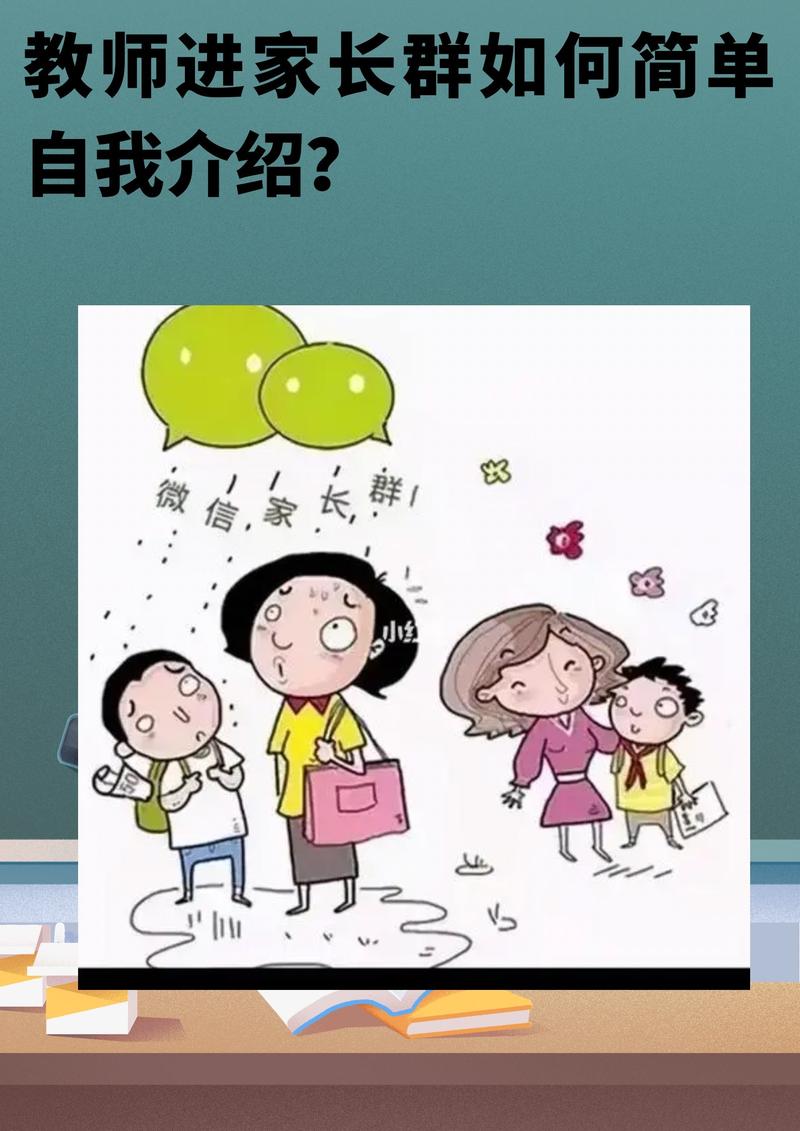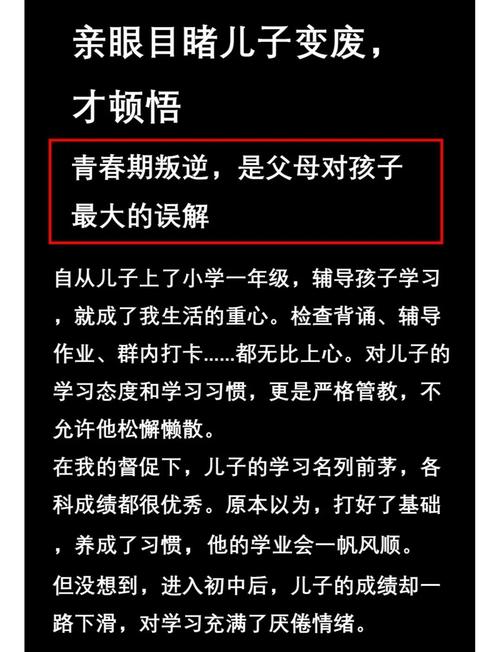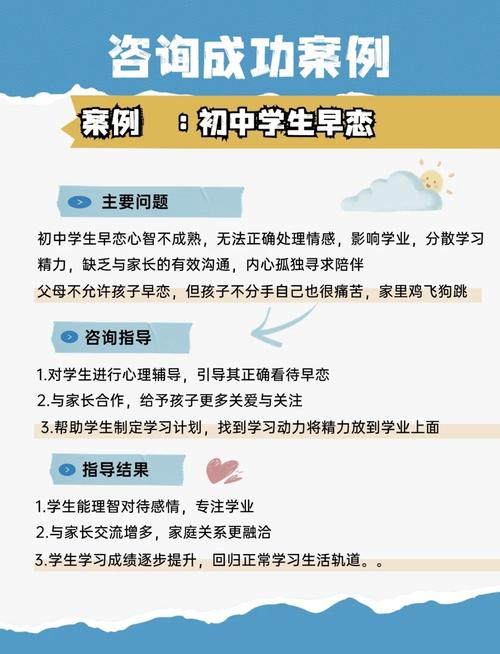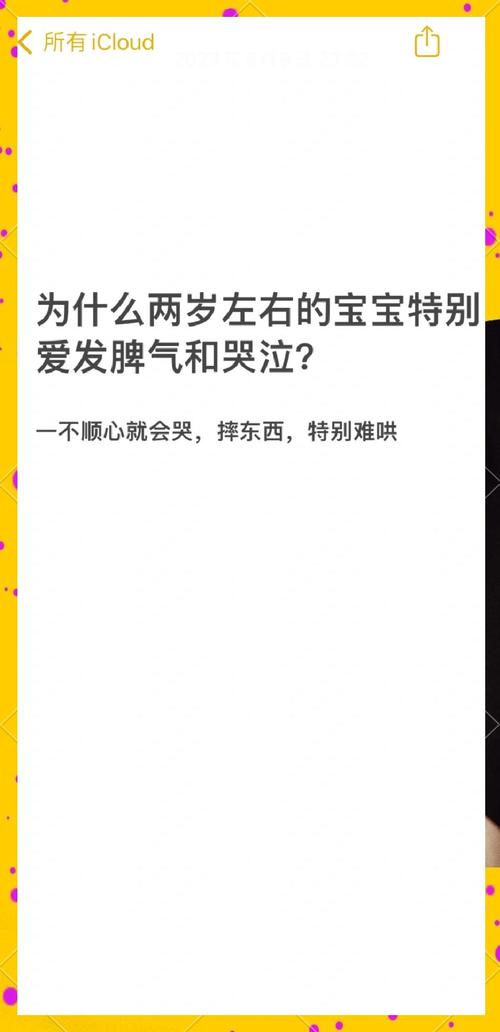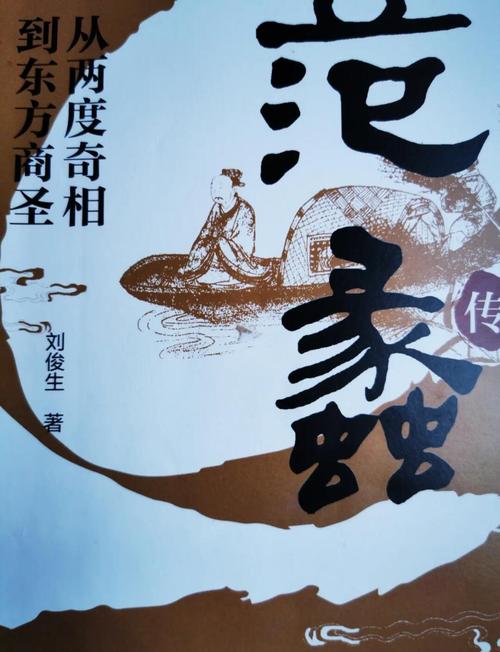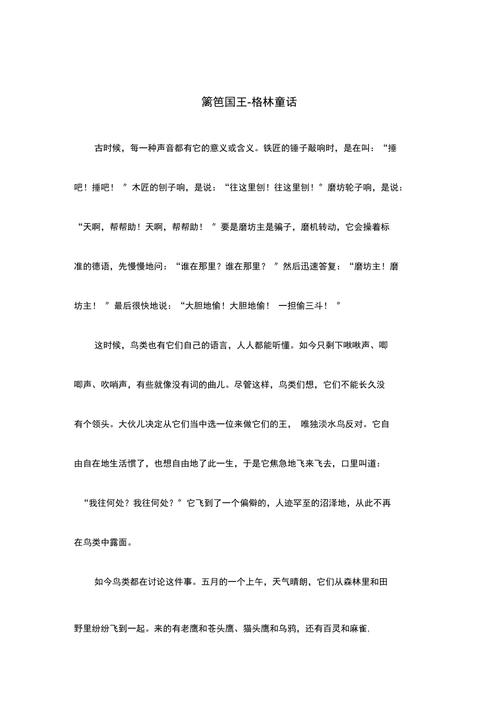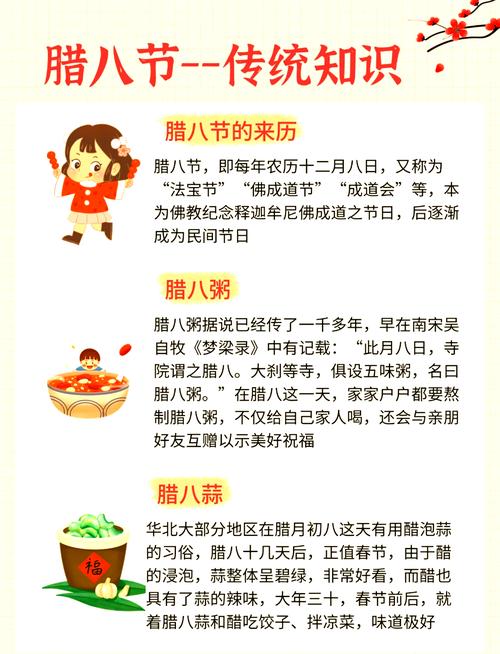在江户时代的街头巷尾,当行灯初上时,总能看见围坐听故事的人群,那些口耳相传的"百物语"中,契约与背叛的叙事犹如穿行于幽冥的丝线,将人世与异界紧紧缠绕,这些被称作"日本聊斋"的民间怪谈,以诡谲的想象构筑起独特的道德法庭,在妖异奇谭的外衣下,深藏着对契约精神的敬畏与警示。
异界契约的文化基因
日本列岛的神道教传统赋予万物以神灵,从巍峨富士到庭前石灯,皆可成为"契约"的见证者,这种泛灵信仰在《古事记》中已见端倪,天照大神与须佐之男的"誓约生子"仪式,实为最古老的契约范式,佛教传入后,因果轮回的观念与本土的"言灵"信仰相互交融,使得每句诺言都如同刻在三途川畔的碑文,具有跨越生死的效力。
在《今昔物语集》的"鬼怪卷"中,人与异类的契约往往通过"血判状"确立,这种以指血为印的仪式,暗合神道教的"禊"观念——血液既是生命的象征,也是污秽的载体,当人类以鲜血缔约时,实则是将灵魂抵押给不可知的存在,京都醍醐寺珍藏的《百鬼夜行绘卷》中,那些手持契约文书的妖鬼,面容狰狞却神情肃穆,正是这种神圣性的视觉化呈现。
室町时代的阴阳师文献记载,违背契约者的名字会被录入"泰山府君"的冥簿,这种源自中国道教的神灵信仰,在日本演变为独特的冥界审判体系,京都下鸭神社现存的"式神契约书",详细规定了违约者将承受"七世厄运",其严苛程度远超现世法律。
血色契约的现世报应
《雨月物语》中"菊花之约"的故事,将武士道的"义理"推至极致,两位武士盟誓重阳相会,当其中一人因冤狱无法赴约,竟自刎化为鬼魂践诺,这个被多次改编的经典故事,在江户町人的演绎中逐渐衍生出更复杂的版本:某商人受托保管友人之子,却因贪念将孩童卖作人柱,二十年后,商人家族接连暴毙,每具尸体手心都攥着干枯的菊花。
在东北地区的"子育幽灵"传说里,难产而死的母亲与山神立约,以永不转世为代价换取哺育婴孩七日,当家族违背诺言提前下葬,暴走的母魂化作"产女"妖怪,每到雨夜便抱着石臼徘徊村道,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百鬼屏风"中,这个披头散发的形象始终紧攥襁褓,空洞的眼窝里淌着血泪。
九州的"海女契约"更显诡谲,渔村少女向龙宫使者承诺献祭三年渔获,却在丰年私自截留,次年盂兰盆节,海面浮起无数契约木牌,每个牌位都对应着失踪的村民,长崎县现存的"龙宫堂"遗址中,仍可见到当年渔民刻在梁柱上的悔过书,字迹深深嵌入木纹,仿佛在警示后人。
幽冥审判的教育隐喻
这些怪谈中的契约守护者,实为传统社会的道德仲裁者,当《御伽草子》中的狸猫化身契约神,用妖力惩罚背信者时,反映的正是町人阶层对商业诚信的焦虑,大阪商人至今保留着在店铺供奉"契约狸"塑像的习俗,雕像左手持算盘右手握契约,暗含"利义两全"的经商哲学。
现代教育研究显示,怪谈中的超自然惩罚机制,实为前近代社会的重要规训手段,在识字率不足20%的江户时代,这些口传故事比《六谕衍义》更具传播效力,东北大学民俗学研究所的田野调查表明,直到昭和初期,青森县仍保留着"契约破りは河童に抓られる"(违约会被河童抓走)的童谣。
在当代契约社会,这些怪谈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早稻田大学伦理课将《牡丹灯笼》纳入教材,引导学生思考数字时代的"电子契约"精神,故事中阿露小姐的亡灵执着于婚约,恰似现代人在虚拟世界中的身份认同困境,京都某中学更开发出"怪谈道德课",让学生通过改编古典故事来讨论学术诚信、网络誓言等现实议题。
夜幕降临时,大阪道顿堀的霓虹灯牌次第亮起,那些浮世绘风格的妖异图案在光影中若隐若现,当代人虽不再相信字面意义的"鬼怪契约",但深植于文化基因中的敬畏之心从未消退,从纸质文书到区块链技术,从血判状到电子签名,变的只是契约的形式,不变的是对"诺言重于生死"的价值坚守,那些游荡在怪谈中的幽冥使者,终将以文化记忆的形式,继续守护着人类文明的信用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