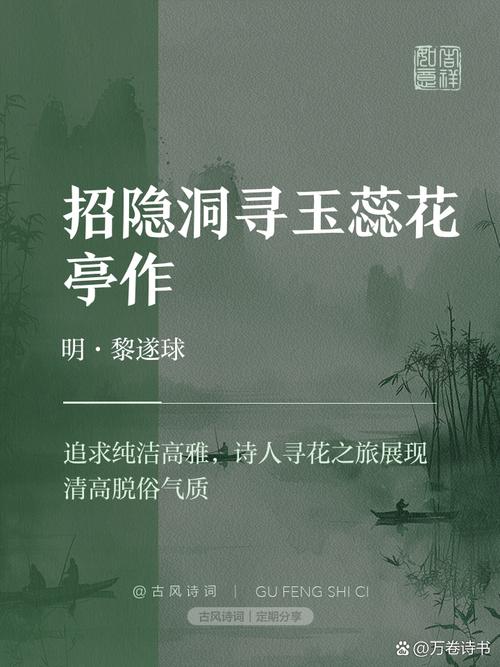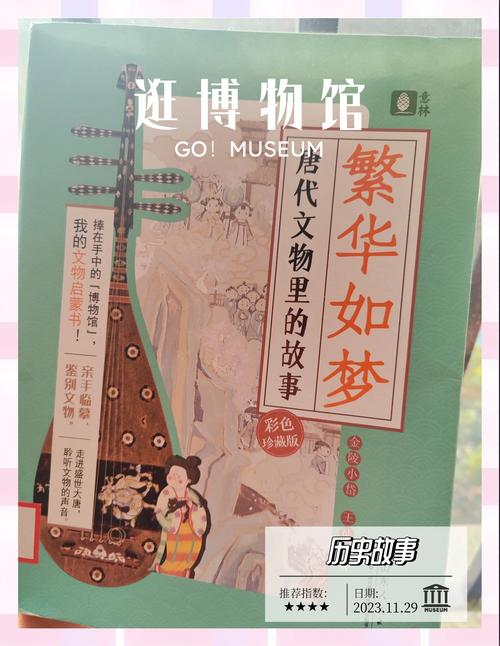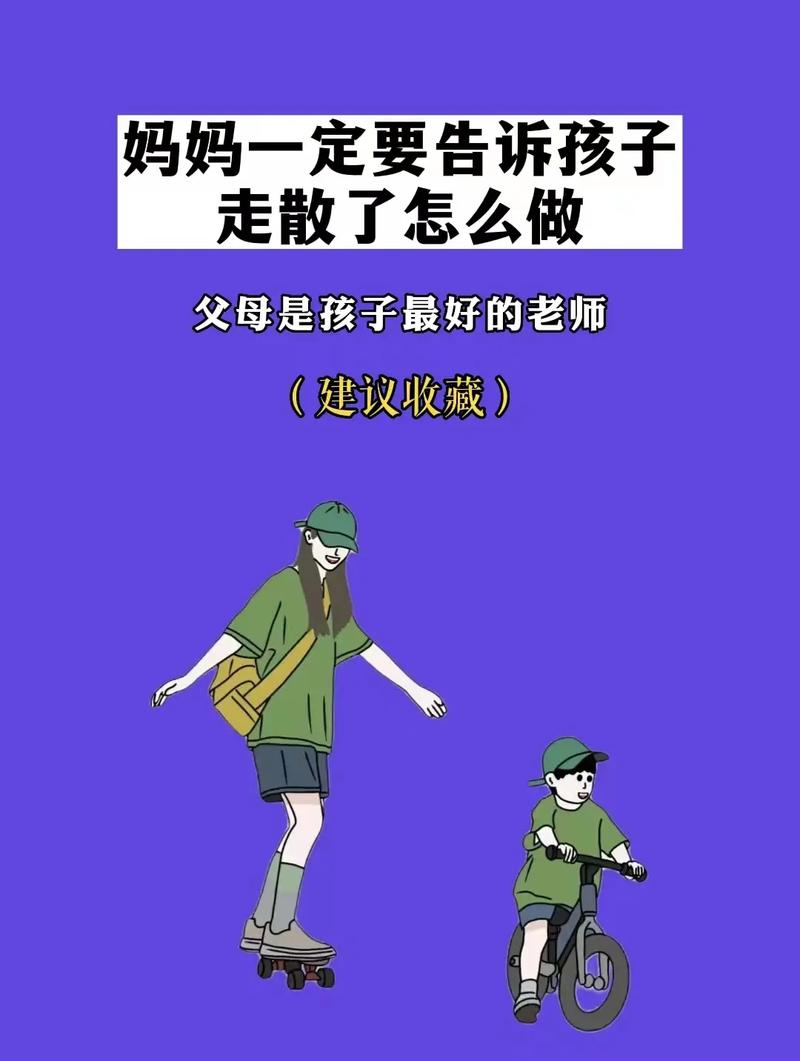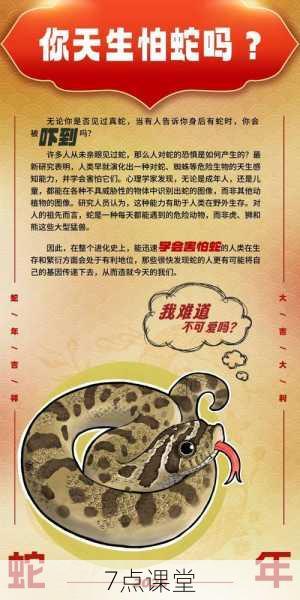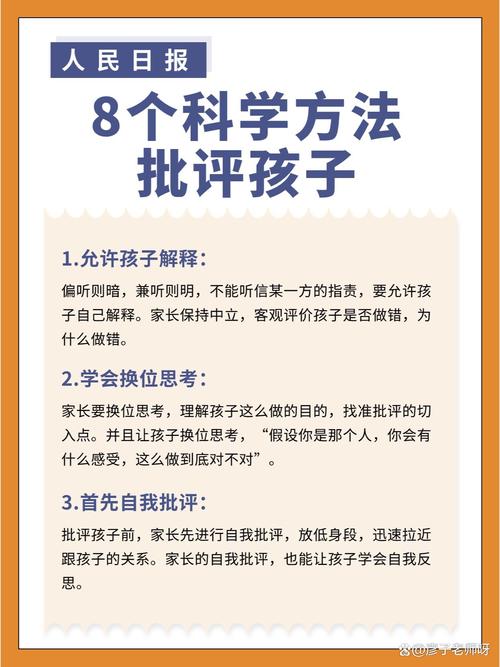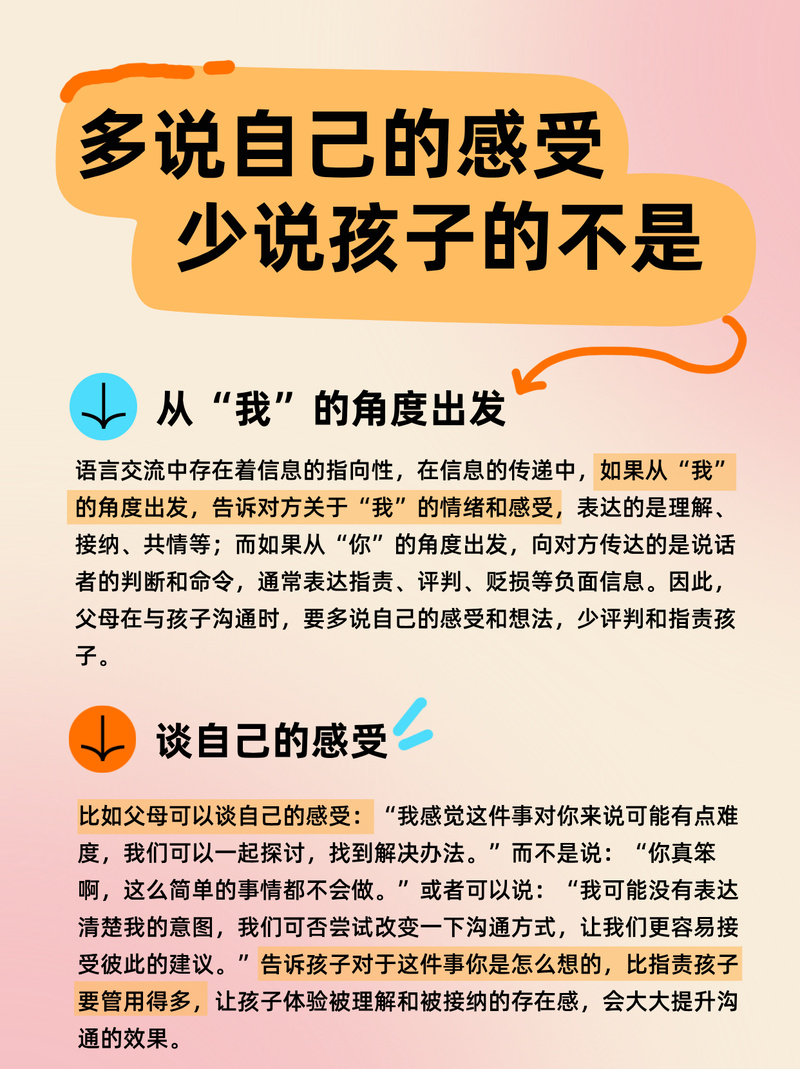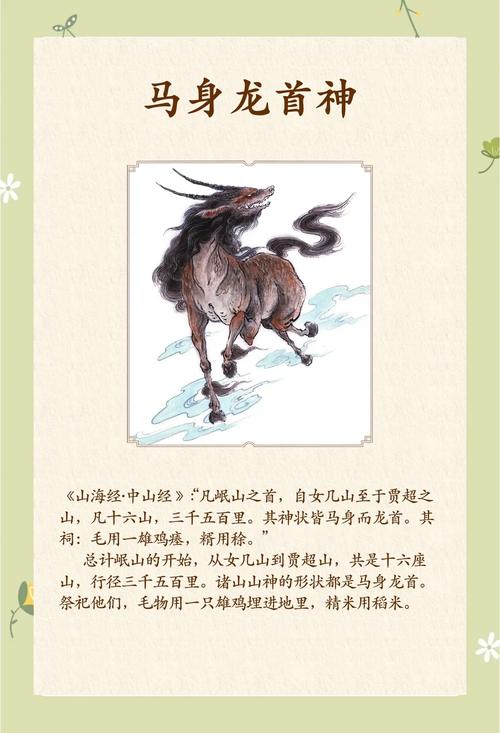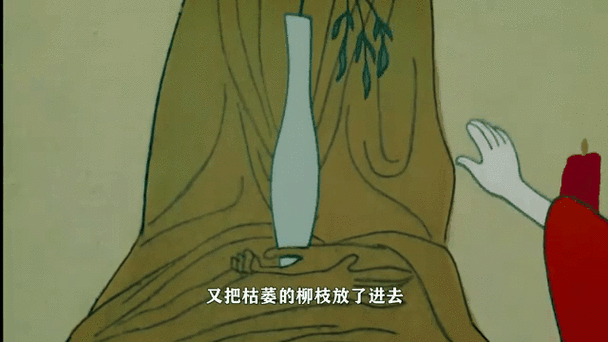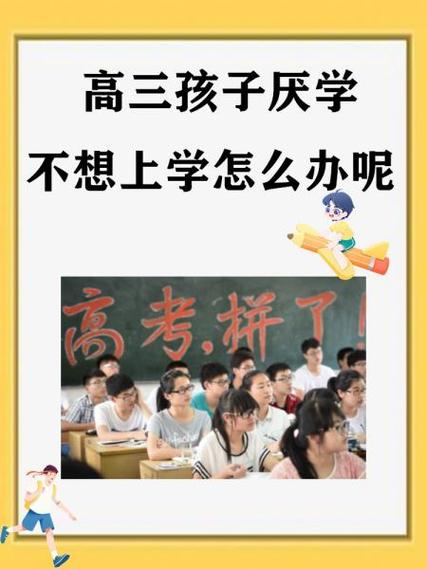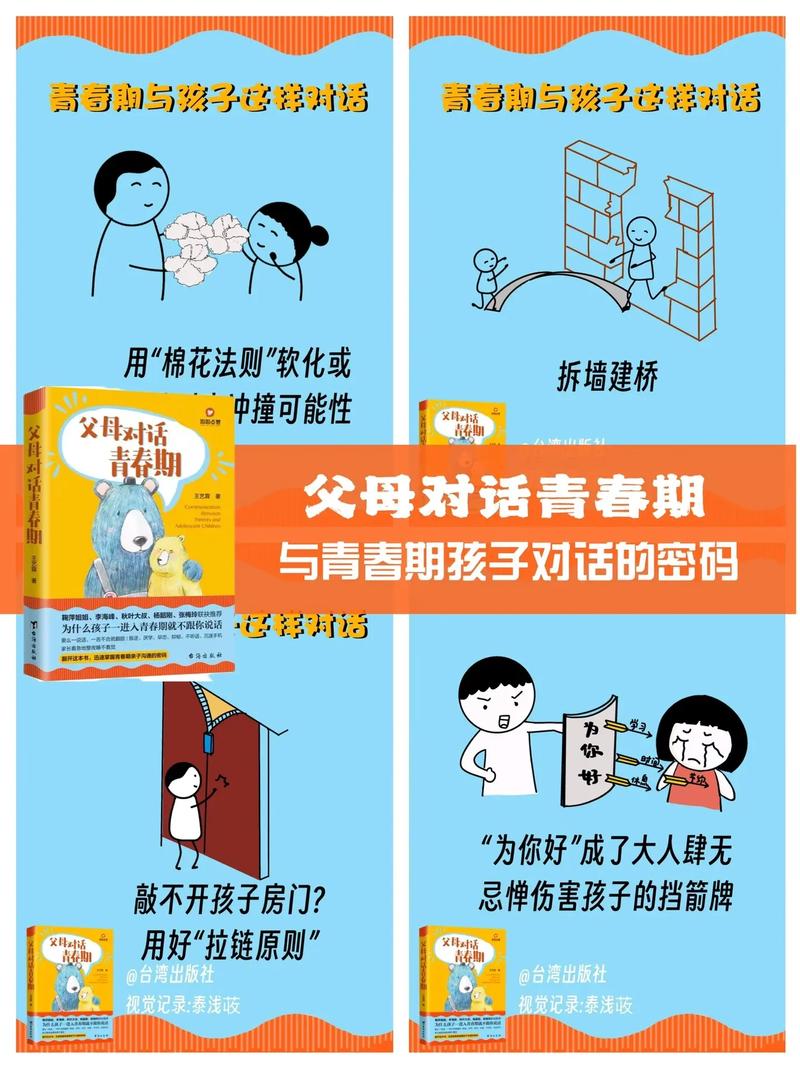在长安城外的唐昌观遗址,一座青砖黛瓦的六角凉亭静立千年,这座被历代文人反复吟咏的玉蕊亭,不仅承载着唐代最富传奇色彩的花卉记忆,更见证了中国古代园林文化中"以花立亭"的独特传统,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十九株玉蕊花与一座亭台交织出的文化图景,恰似一幅徐徐展开的盛唐气象长卷。
琼枝玉蕊的盛世绝唱 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5),长安城东南隅的唐昌观因十九株玉蕊花名动京师,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稹在《酬严给事闻玉蕊花下有游仙》中写道:"弄玉潜过玉树时,不教青鸟出花枝。"这段诗注记载了当时轰动京城的奇观:每当玉蕊盛放,便有仙娥装扮的女子在花间流连,引得士庶争睹,这种被唐人视为"瑶池仙品"的花木,其花型如雕玉琢琼,夜间绽放时清香袭人,晨露未晞即随风飘散,这种转瞬即逝的美学意象,恰好暗合了盛唐文人"刹那永恒"的生命感悟。
从植物学角度考证,玉蕊花(学名:Barringtonia racemosa)属玉蕊科常绿乔木,原产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唐代气候较今温暖湿润,长安城年均气温比现代高1-2℃,这为热带植物的北移提供了可能,宋代《证类本草》记载其"花白,六出,心黄,气清香",与现存海南岛野生玉蕊特征相符,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在唐代文献中频繁出现的珍稀花木,却在宋元之后的中原典籍中逐渐消失,只留下"玉蕊"二字在诗词中作为典雅意象流转。
从仙界传说到底层叙事 玉蕊亭的文化密码,深藏在多重叙事结构的叠合中,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的仙女下凡传说,赋予了玉蕊花超自然的灵性;白居易"嬴女偷乘凤去时,洞中潜歇弄琼枝"的诗句,则将道教升仙思想融入花卉审美,这种"以花通仙"的想象,实则是唐人追求永恒的精神投射,而当我们拨开神话迷雾,从现存的唐昌观遗址出土的柱础规格推断,当年围绕十九株玉蕊花建造的园林建筑群,其规模远超普通道观配置,暗示着皇家贵胄的深度参与。
更耐人寻味的是底层工匠的营造智慧,玉蕊亭独特的六出飞檐造型,暗合玉蕊花的六瓣花型;亭柱间距经过精密测算,既保证观花视野的最大化,又形成空气环流以延长花期,这种将建筑力学与植物特性完美融合的实践,展现了唐代工匠"道法自然"的营造理念,近年考古发现的亭基排水系统,更揭示出唐人已掌握利用地下水脉调节小气候的先进技术。
文化符号的嬗变与重生 随着晚唐气候转寒,玉蕊花在中原地区的栽培逐渐绝迹,北宋周师厚《洛阳花木记》已将玉蕊列为"昔有今无"之列,但文化记忆仍在延续,苏轼"后土祠中玉蕊香,扬州芍药更无双"的类比,王安石"玉蕊亭边集翠娥,宸游为此驻雕鞍"的追忆,都在重构着这种消失花卉的文化意象,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江南园林中出现的"玉蕊"称谓,实则是文人对西府海棠、垂丝海棠的意象移植,这种文化符号的嬗变恰恰印证了中华花卉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当代学者在海南岛发现的野生玉蕊群落,为破解历史谜题提供了新线索,这些生长在热带海岸的红树植物,每年端午前后绽放穗状花序,与唐代文献记载的"夏夜吐芳"特征完全吻合,更令人惊叹的是,其花瓣在黎明前自动脱落的现象,竟与《长安志》中"夜开昼落"的描写惊人一致,这种跨越千年的生物学印证,不仅解开了历史悬案,更揭示了古代植物栽培技术的高度成就。
亭台花木的现代启示 玉蕊亭遗址保护工程中发现的唐代瓦当纹样,呈现独特的缠枝玉蕊图案,这种将建筑构件与特定植物绑定的装饰传统,对当代景观设计具有重要启示,北京大观园复建工程借鉴此理念,在蘅芜苑设计中融入大量杜若纹样,创造出建筑与植物对话的空间语言,而苏州博物馆新馆的紫藤花架,正是对"以花立亭"古法的现代转译。
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玉蕊花的重现更具特殊意义,华南植物园的迁地保护项目,成功实现了玉蕊在北回归线以北地区的栽培,科研人员发现,这种植物对重金属污染土壤具有显著修复作用,其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的双重属性,恰与古人"观之以美,用之以德"的造园思想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当我们在玉蕊亭遗址抚触那些刻着缠枝纹的柱础,仿佛能听见盛唐的风穿过玉蕊花枝的轻响,这种消失又重现的东方花木,不仅承载着中华文明对自然美的极致追求,更蕴藏着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在当代城市景观日益同质化的今天,重读十九玉蕊花与玉蕊亭的故事,或许能为我们提供重塑"诗意的栖居"的文化密码——那是在钢筋森林里寻找自然韵律的勇气,也是在科技时代守护文化记忆的自觉。